“追忆者寻找的也许不只是那个人,而更多时候是过去的自己和已逝的青春。”
——胡康、郑一卉:《寻忆陌生人:数字记忆实践中的“联结”与“无法联结”》,《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6期,页119-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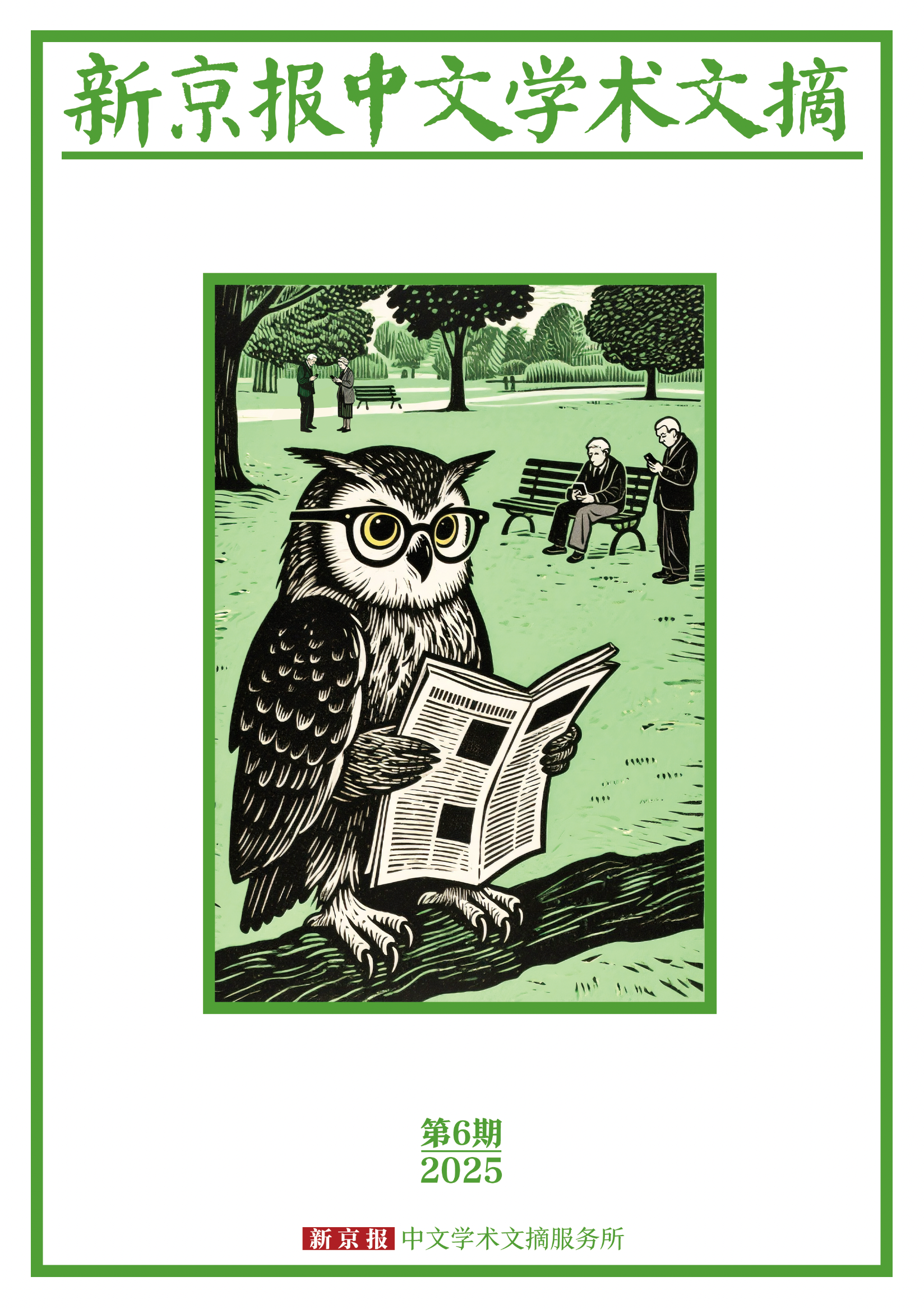
本期评议:黄典林
文本摘选:罗东
在当代,书籍之外,刊于专业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是知识生产、知识积累的另一基本载体。《新京报·书评周刊》在图书评介的基础上试拓展“学术评议和文摘”这一全新的知识传播工作,筹备“新京报中文学术文摘服务所”,与期刊界以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文摘刊物一道服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我们希望将近期兼具专业性和前沿性的论文传递给大家,我们还希望所选论文具有鲜明的本土或世界问题意识,具有中文写作独到的气质。
此为第6期。第二篇论文的作者胡康、郑一卉收集并分析了一种别样的网络寻人活动。试想,某天我们翻出旧照片,看到一旁站着某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即便当年只是短暂相处或萍水相逢,关于那个地方或那段岁月的记忆却也当即被唤醒,自此无限感慨。于是有人希望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障碍,借助网络及其算法“捞人”,重新建立联结。或成功,或失败,作者将其结果概括为“联结”与“无法联结”,记忆在此间得到复现和重建。
以下内容由《国际新闻界》授权转载。摘要、参考文献及注释等详见原刊。
作者|胡康郑一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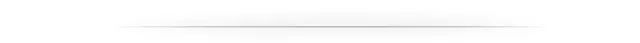

电影《你好,之华》(2018)剧照。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
在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眼中,体外化(exteriorization)的媒介介入人类记忆之后,有机的记忆便被附上了“无机”的特征(胡康,2024)。例如,蜡板、笔墨等媒介将抽象记忆转译为外在的具象符号,从而实现传播与贮存效果。面对记忆所呈现出的无机化趋势,柏拉图等智者开始担忧,认为将媒介奉为记忆的圭臬不利于人类“记忆力”的培养与维持,甚至会使大脑失灵(胡康,郑一卉,2024a)。对于反对者而言,媒介只是存储记忆的工具,过度依赖媒介,人会丧失自身的能动性。不过,随着数字媒介技术的诞生与应用,固化的物质记忆转变成动态分布的“数字记忆”(digitalmemory)(Hoskins,2011a),记忆发生了从“静态存储”转向“动态联结”的根本变化。在此语境中,不仅“记忆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而且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相互联结与交互也使“记忆力”不断得到巩固。
当下,人类已“无法脱离媒介而生活”(Hoskins,2011a),即使选择“断网”“断联”,社会个体仍然被各类媒介所包裹。对此,马克·杜资(MarkDeuze)(2011)提出了“媒介生活”(medialife)这一概念,用以表明媒介已在各个方面渗透于人类的生活结构之中。从记忆的视角来看,人的“媒介生活亦是记忆生活”(Hoskins,2011a)。因媒介而掀起的“记忆热潮”(memoryboom)改变了过往“记忆稀缺”的情形,多元的记忆被载入时间之册中,至此,人们迎来了以记忆过剩为表征的“后稀缺”(post-scarcity)时代。为了更好地应对与传播记忆,诸如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以算法机制对这些海量记忆内容展开了筛选、分类、加权,使得某些记忆脱颖而出,成为焦点、热门。其中,便有着这样一种“另类的记忆”——关于“陌生人”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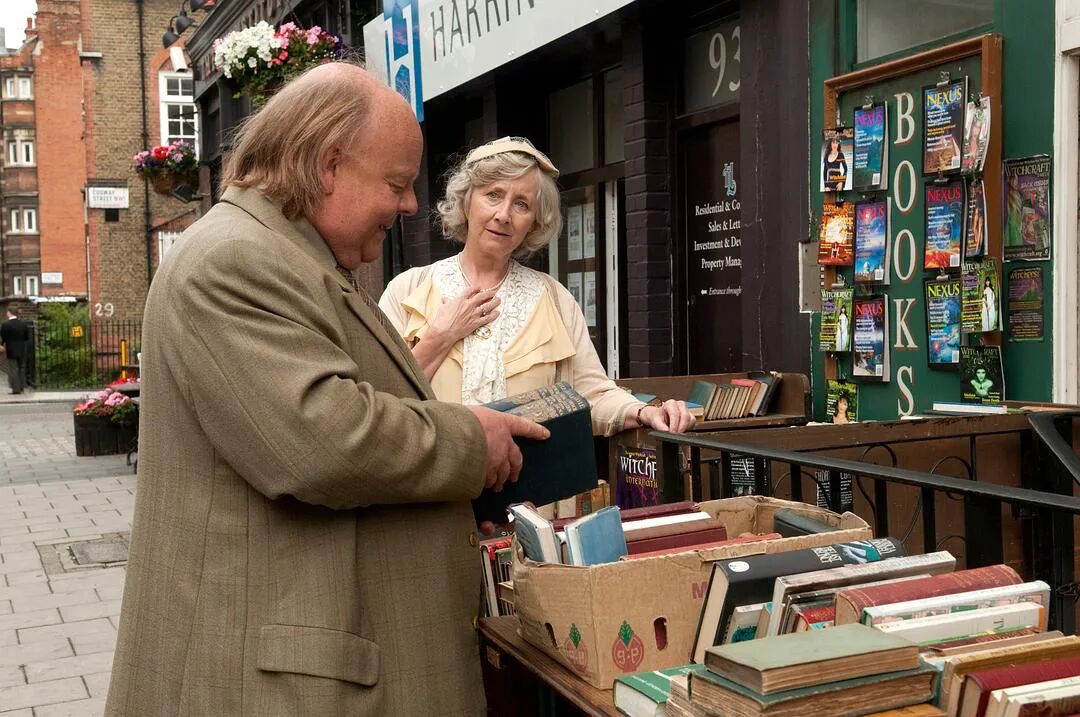
电影《遭遇陌生人》(YouWillMeetATallDarkStranger,2010)剧照。
在传统认知中,记忆往往与自己或身边的熟人相关(Skowronskietal.,1991),记忆的“认知深浅是判定人我亲疏的重要依据”(黄泰轲,2018),人们也总是与亲密的人分享、交流记忆,而非陌生人(French,Garry&Mori,2008),因为陌生人代表着关系中的未知性与不确定性,可能会破坏个体正常的生活规律与记忆秩序。于是,陌生人成为被记忆排斥的“无用的生命”(wastedlives)(Bauman,2004),社会分析话语中也出现了以“我们-他们”“熟人-陌生人”为代表的二元分析框架,明确划分出彼此之间的生存与活动边界。
但是,诸如抖音、小红书此类以视听(audio-visual)为主要传播形式的社交平台中却出现了“寻忆陌生人”的另类记忆实践。许多用户化身为追忆者,在这些平台中以数字形式上传家里的老照片,希望通过网络和陌生网友的力量找寻到老照片中那些与自己“擦肩而过”或曾经“萍水相逢”的陌生人。
记忆的一大关键在于“重复”,被追忆的对象通过反复出现,从潜意识浮现到意识,从而获得关注(WordPress,2015)。学习的过程总体来说就是回忆的过程(Plato&Cooper,2002:111、114)。人们只有通过不断巩固、回忆,被追忆的对象才能够得到存续,否则便会被忘记,变成不可访问的记忆。不过,保罗·力克尔(PaulRicoeur)(2000/2004:416)认为,很多早年的记忆,如童年时期的记忆并没有完全消失,而只是暂时无法触及。对此,“梦幻记忆”(reveriememory)强调,记忆并不是纯粹“自觉”的,个体能够借助某种触发条件在无意识中“漂回”到过去的场景中,实现记忆的重新联结(reconnection)(WordPress,2015)。对于那些旧照片中的陌生人而言,他们与追忆主体早已被时间长河所冲散,但却因为旧照片的物质“刺激”而又重返追忆主体的意识之中。旧照片成为记忆的触发器,帮助人们重新与过去联结。不过,从本文所关注的记忆实践来看,追忆主体似乎并不满足于自我臆想式的“回忆”,而是想要借助社交平台展开寻人活动,以记忆公开的方式“再续前缘”。在此类媒介化的期待与实践中,社交平台进而成为“记忆聚集”(culsterofmemories)(Jacobsen,2024)和网友们展开“联结行动”(connectiveaction)(闫文捷,李红涛,2022;Bennett&Segerberg,2012)的数字空间。
“数字记忆研究既要在‘智识挑战’层面揭示实践逻辑,也要在‘社会意义’层面发掘并彰显实践智慧。”(李红涛,2024a)对经验案例展开学理化的分析与思考是对实践的再度升华,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记忆,记忆做了什么”(whatmemoryisandwhatmemorydoes)(Hoskins,2017a:7)。“寻忆陌生人”的数字记忆实践必然是新鲜而有趣的,但更重要的是挖掘其背后所潜藏的学理意涵与社会文化效应。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几个研究问题:社交平台在该记忆实践中发挥着怎样的联结性作用?被追忆的陌生人如何与记忆实践主体在当下产生联结?联结之后发生了什么?又能给予何种学理启示?
二、理论工具与研究设计
为了更好地对“寻忆陌生人”这一联结式的记忆实践展开学理思考,本文主要以安德鲁·霍斯金斯(AndrewHoskins)的“联结记忆”(connectivememory)为理论工具。“联结记忆”依托于“联结转向”(connectiveturn)的研究背景而产生(Hoskins,2011a),是一种“敏化”(sensitizing)的理论工具,能够帮助研究者在窥探现象的过程中,透视现象的内核,将其向更具学理性的方向推进(黄顺铭,陈昭博,2024;李红涛,2022;Hoskins,2011b)。数字媒介技术的普及与应用不仅使得人与人之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跨时空、跨文化联结,而且消解了“人-物”之间的交互隔阂,人、技术、平台等皆可相互联结,这亦是“深度媒介化”(deepmediatization)(Hepp,2020:5)的本质显现。
在传播的联结转向中,横亘于“生理”“社会”“文化”之间的研究区隔被打破(Hoskins,2011a),为学者探索记忆注入了更多动能,带来了更多视角。进一步来看,以时间为表征的记忆深受联结的影响,联结转向改变了记忆的生成、回顾、贮存、传播的方式(李红涛,2022),对记忆的本体论形成挑战,具体而言:数字媒介所发挥的万物互联的效果打破了时间性层面“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边界,记忆从静态的存储物转变为一种持续流动的联结和再生产过程。在数字媒介的加持中,过去的记忆可以随时被召唤到当下,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在人与人的交流互动中产生全新的内容与意义。
联结记忆所具备的“动态性”“实时性”“关联性”“开放性”为我们思考“寻忆陌生人”这一数字记忆实践提供了条件。一方面,研究者将基于联结记忆的典型特征探索社交平台在与人(包括追忆者、网民、被追忆者)的互动中是如何铺就“联结轨迹”的。另一方面,研究者将深入挖掘联结之后所带来的现实结果与文化效应,并在这一过程中进行否思,即借助“寻忆陌生人”记忆实践案例来检验、反思“联结记忆”理论本身,以期丰富联结记忆的学理意蕴。
在研究设计方面,本文将采用参与式观察与访谈法展开研究。在参与式观察方面,研究者选取了抖音和小红书两大社交平台为线上观察点位。整个观察流程总体分为三个阶段,即观察前期、观察中期、观察后期。在观察前期,研究者分别在两大社交平台上以“寻人启事”“寻找陌生人”“捞人”“全网寻人”等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以人工清洗的方式去除不符合本文研究主题的视频或图文内容,将符合主题的内容进行收藏,以便后期进行分析。在观察中期,研究者主要通过观看视频、阅读图文帖的方式搜集有用信息,在评论区中择取网友观点,全程用截图或备忘录的方式记录下博主或网友的自述以及研究者的所思所感,并在两大平台中分别设立收藏夹,收藏值得重点关注的博主的内容。在观察后期,研究者基于先前的观察,开始以“私信”的方式向29位博主和网友征询访谈意愿,并最终获得14位访谈对象,分别将他们编码为F1~F14。

电影《久别·重逢》(2024)剧照。
在访谈前,研究者以文字聊天的形式与访谈对象交代了研究的相关事宜,并承诺不公开个人信息。访谈时,研究者主要围绕“寻忆陌生人的原因”“寻忆陌生人过程中的故事和感受”“寻忆陌生人的结果”等话题展开交流,时长维持在120分钟以内,并全程进行录音。需要说明的是,在后期补充材料时,研究者以文字的形式与受访者进行了交谈。
三、社交平台铺就“联结轨迹”
长久以来,记忆被简单地划分为两种认知模式:记忆要么被视为一种会随时间流逝而不断消减的物,要么被认为是残缺的存在,总是零散而破碎的(Hoskins,2011b)。对此,霍斯金斯发出批判,指出两种认知不利于人们在数字时代把握记忆的奥义。在联结转向中,他把记忆看做是人、媒介、事件、社会、文化等相互作用、持续互动的产物,且这一生产过程没有终点,是一条乃至多条无限延续的轨迹(trajectories),每一次或大或小的联结与互动都会赋予记忆全新的意义(Hoskins,2011a)。在“寻忆陌生人”的记忆实践中,社交平台是建立联结的主要场所,始终处于“运动”(in-motion)状态(Hoskins,2011b)。有鉴于此,本节将围绕社交平台,探索其铺就联结轨迹的具体路径和方法。
(一)作为记忆联结的触发器
数智媒介时代的记忆实践已无法脱离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联结作用。从非人类行动者层面来看,诸如旧相册、旧照片等传统媒介和手机、电脑、社交平台等新兴媒介成为人们在赛博空间中展开“寻忆陌生人”记忆实践的重要基础。不过,在不同时间性层面,追忆者利用这些媒介展开记忆实践的表现亦不尽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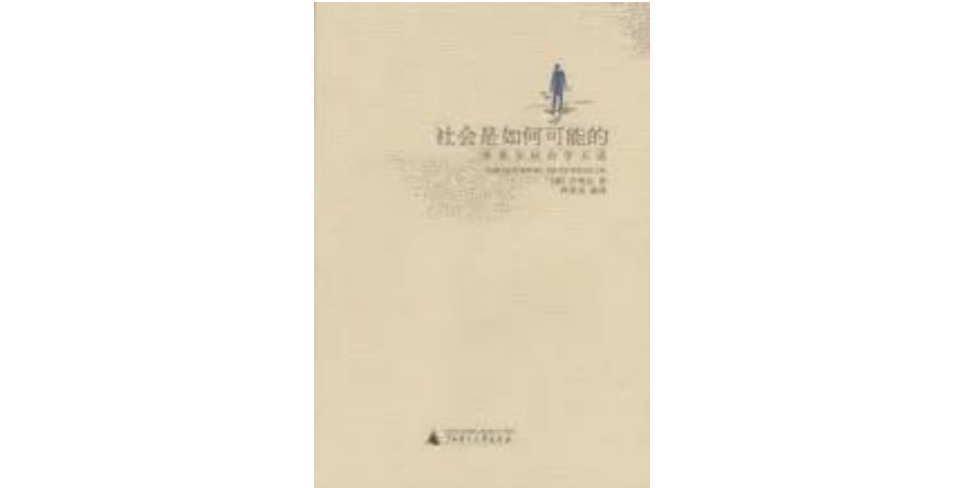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
译者:林荣远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
人总是会被融入客观物质之中,以不同的形式存在(齐美尔,2002:67)。从“过去”来看,追忆者利用相机捕捉即刻流逝的东西,如人的笑容、表情、动作、姿态等,借助照片实现了它们的离身(disembodiment)持存。到了“当下”,作为“回忆型的仓储库”(reminiscencedatabases)(黄顺铭,陈昭博,2024),旧相册如同范·迪克(VanDijck)(2007:17)眼中的“鞋盒”,或者说“家庭媒介”(familymedia),其中装满了代表过去,横跨不同时间间隔的“旧照片”,为当下的“跨时空复现”奠定了基础。这些旧照片以静态图像贮存着个体的过往回忆,照片中的人物、场景被当下的追忆者重新定位(relocated),在人的主动翻阅与回忆中成为联结过往的触发器,并以此激活相应的记忆。
“(旧相册)中有一张合照我记得很清楚,里面有一个小女孩,我妈说我小时候跟她玩得特别好。但如果没有这张照片,我根本不记得了……这也是我为什么发到网上的一个原因,想知道(我和她之间)发生过哪些事情……现在就算在街上看见,也根本不认识吧?”(F6,2023年5月10日)“这些记忆很模糊。”(F9,2023年7月14日)对于追忆者而言,旧照片所触发的仅是零散的记忆碎片,而社交平台却成为他们求助的关键媒介。在实时连接的社交平台中,追忆者以数字再照或扫描的形式将纸质版的旧照片上传至赛博空间,在这些视频或图文帖中,#寻找陌生人、#老照片寻人启事、#捞人等标签成为追忆者扩大可见范围的主体性尝试,而平台中的点赞、转发、评论、帮上热搜等功能则提升着追忆者与被追忆对象之间联结的可能性,在记忆的公开与分布中试图促成“联结性见证”(connectivewitnessing)(韩婕,李红涛,刘于思,2023)。
除了现实生活中不经意的发现,社交平台中的算法推荐机制亦是“邀请”许多网友化身为追忆者,加入“寻忆陌生人”实践队伍的一大触媒。
一开始是同事先刷到跟我说的,然后下班晚上我刷抖音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些视频……我本身就很感性,(所以)我也翻出了很多旧照片出来,选了一张之前玩漂流的时候跟队友们拍的合照……大家也没留联系方式,现在想想还是挺可惜的,毕竟一起度过了那么惊险的时光,也算相识一场。所以我就也尝试着发到网上,看看能不能找到吧!(F1,2023年12月23日)
存于数字媒介端口的照片在算法提供的滚动模版中以音乐、滤镜、颜文字等多模态元素叠加的形式被重新包装,并得到故事化呈现,因时间流逝而逐渐模糊的记忆在自动生成的数字化记忆中得到稳固,生理记忆的演化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技术的改写,对于陌生人的察觉也在此媒介过程中得到激活或增强。这种看似“偶然的发现”(serendipitousdiscovery)实则受到技术的有意操控,“它们总会在合适的时间向用户提供正确的内容”(Lohmeier,Kaun&Pentzold,2020)。可以说,平台算法成为记忆活动开展的“弄潮儿”,“日益成为记忆的技艺(techneofmemory),它们以其承受力和能力,呈现过去,并将过去带入现在”(Kalin,2012:170)。
(二)在开放与在线中形塑“纵向的共时性”
社交平台超越了传统的“档案”(archive)形式,在联结转向中将“档案空间”转变为“档案时间”(Hoskins&Halstead,2021)。研究者在观察时发现,与以往静态、封闭且中心化、机构化的档案不同,抖音、小红书一方面向所有用户开放,存储着海量的个体记忆,得到传播与展现的内容不再局限于官方与精英,微观的个性化记忆获得了叙述过往与被承续的权利和机会(Prey&Smit,2019:209-220)。而且,这种数字化的档案(digitalarchive)中贮存着许多不同的人际关系。不仅亲朋好友等熟人可以在社交平台中进行线上联结,彼此分享内容、产制记忆,而且陌生网友之间亦能够通过多元的交互方式“结缘”。
在博主“寻忆陌生人”时,尽管网友之间互为陌生人,但他们依旧会主动加入这一实践网络之中,通过“接力传播”(如点赞、评论、转发、帮上热搜)永不停歇地向外延展记忆的可见范围。正因如此,这些“过去”的记忆永远不会“休眠”,“过去”永远都处在“当下”。
以博主“夏望”在2023年2月15日于抖音发布的“寻忆陌生人”视频为例:虽然该数字记忆实践已过去近2年的时间,但是通过该视频的数据可以发现,这个原本早已成为“过往”的事件在网友的持续关注与互动中依旧活跃在当下,其中最为直接、明显的证据便是不断增多的点赞量与新鲜的评论内容。“说实话这一套放在现在都还没有过时”(ID:lllivngenge;评论时间:2023-02-15)“科技的意义”(ID:独;评论时间:2024-11-13)“寻找13年前拍照的女孩”(ID:小刘同志;评论时间:2025-05-06)……
若从比较的视角回望传统的档案,那些早时被存储的记忆材料“具有某种残片的、一种存储记忆的特点,还没有被意义的产生而照亮,但是也没有被遗忘和压抑完全地排挤掉。就像阁楼里边的破烂儿,还存在着,但是很少被检视,这种记忆固着在意识的阴影里”(阿斯曼,2009/2016:178),等待被人们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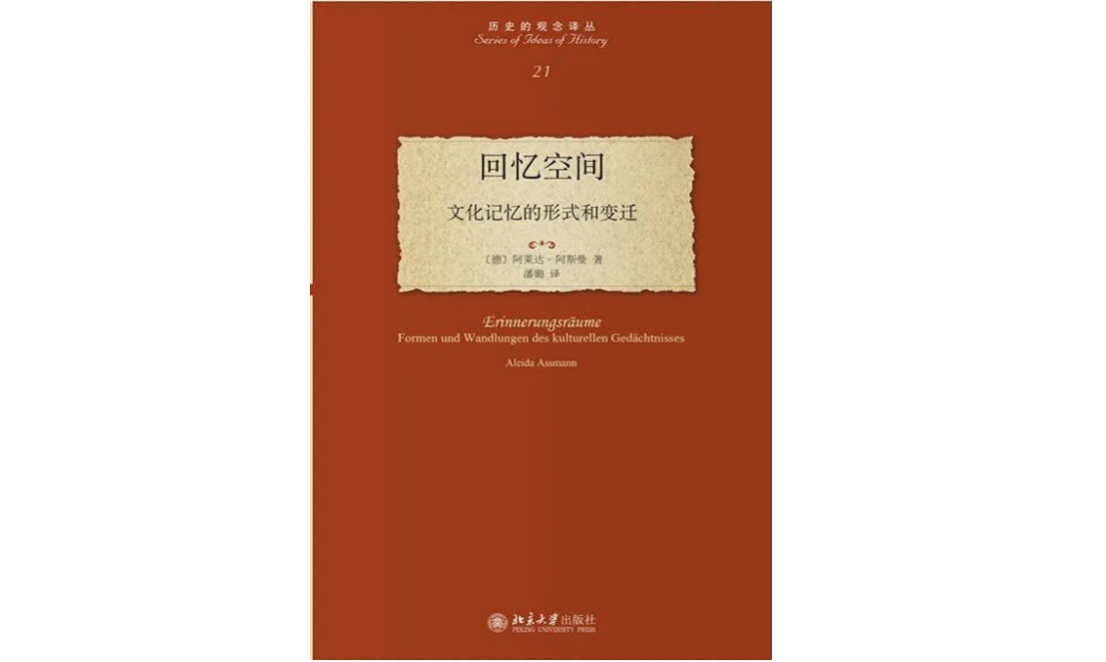
《回忆空间》
译者:潘璐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
由是观之,即使“寻忆陌生人”实践的起始点位于过去,但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却以长久在线、实时联结的特质不断将过去召唤到当下,不仅过去的图片、帖文、评论可以得到翻阅、接续,而且新的交互内容依然在被一轮轮地产制,在时间流和意识流的作用中形塑出“纵向的共时性”效应(胡康,郑一卉,2024a),不断增强着平台中的记忆微光。对于追忆者自身而言,平台系统的每一次“消息(点赞、评论等)提示”都会激活他们对于这段过往的回忆,他们的“过去”被持续嵌入“当下”,成为一个置入性的时间平行连续统(continuum)。
四、“联结后怎样”:关系建立与记忆续写
互为陌生人是一种普遍的人际关系状态。不仅那些“从未见过”(Lupton,1999)的人是陌生人,而且“见过却没有交际”(Lofland,1973:17)的亦属于陌生人。本文所关注的三类陌生人分别为“陌生的网友”“无交际的陌生人”“有过交际的陌生人”。具体而言:
第一,陌生的网友。在“寻忆陌生人”的实践中,当追忆者将照片公布于网络,“从未见过”(Schwartz,2013:136)的陌生网友将在照片、平台等媒介的加持下形成联结,以不同的方式(如评论、点赞、寻找线索)共同参与寻人实践之中。第二,“无交际的陌生人”。曾经与追忆主体共同定格于旧照片中的“路人”属于“见过却没有交际”的陌生人。这一情况常有发生:个体在给熟悉的人拍照时因过度关注被照对象(如表情是否到位、姿势是否合适等)而会忽视“闯入”镜头中的陌生人,即因过度聚焦于某物而导致“视域遮蔽”。“咔嚓”一下,镜头便会将被照对象与陌生人共同捕捉。第三,“有过交际的陌生人”。此类陌生人较为特殊,他们曾与被追忆者有着或强或弱的交际,但却又因为长时间断联(如失去联系方式)再次变得陌生,有学者将此界定为“熟悉的陌生人”(Jackson,Harris&Valentine,2017)。熟悉的陌生人之间在后期的联结是一种基于过往关联与交往的“重新”联结。这三类陌生人为我们挖掘联结后的故事与效果提供了现实资源,本节也将分别对三类陌生人的情况展开探讨。
(一)建立新关系:与陌生人“联结”
1.与陌生网友联结
与谁讲述、讨论我们个人化记忆的重要性还未得到学界的重视,与熟人分享,还是与陌生人分享会引发不同的效果(French,Garry&Mori,2008)。实践主体借助社交平台展开“寻忆陌生人”是向所有陌生网友公开个体记忆的过程,这时的记忆已经突破了“私人”的框限,具备了社会性的特征。正是因为私人记忆的社会化,使得记忆本身被附上了更为多元的意涵。“寻忆陌生人”成为一种位于个体与集体之间的“诸众记忆”(amemoryofthemultitude)(Hoskins,2017b:86;Virno,2001/2003:25)。
一方面,作为数字档案的社交平台聚合了诸如“寻忆陌生人”的个体化记忆,使其与其他微观记忆在对外公开的条件下共同构成“集合记忆”(collectedmemory),供陌生网友一同欣赏、讨论。另一方面,与网友展开的交互联结又进而催生出全新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memory),这一集体记忆以“寻忆陌生人”为中心,但并不受限于原初记忆,而是围绕“寻忆陌生人”所衍生出的全新集体式记忆。“好多网友都在评论区里留言,有一起帮忙找人的,有在那开玩笑的,还有‘借楼’找人的。虽然大家都不知道对方是谁,长什么样,但都选择聚在一起贡献自己的力量。”(F14,2024年2月10日)“评论区里很多人都在支持我,还有人发私信过来,告诉我线索。现在想想都觉得很美好,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但跟大家有了一段新的回忆。”(F8,2023年9月25日)

“萍水相逢”的陌生人重逢。图为电影《爱在日落黄昏时》(BeforeSunset,2004)剧照。
对于这些相互联结的陌生网友而言,他们不仅共同见证了博主的个体记忆,而且也成为记忆的参与者,共同推动、甚至决定着记忆实践的发展方向。而对于追忆者自身而言,“这些记忆成为自我与他人以及一系列数字应用、平台、网络之间的全新联结、纠缠(entanglement),其所展现的是联结性公众(connectivepublic)之间的相互协作”(Hoskins,2017b:83)。正是这种记忆实践的联结性,使得原本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寻忆故事开始向“第三人称”转变(Hoskins&Halstead,2021),平台的示能、陌生网友的线索提供、信息增补、差异化解读都在相互联结中超越追忆者自身的叙事力量,“一旦故事公开,所有人都可以讲述这个故事”(Hoskins&Halstead,2021)。社交平台不再简单扮演“记录员”的角色,凡是触达这一记忆的陌生网友也不再简单地作为“旁观者”,而是共同成为此次记忆实践和故事的组成部分。
2.与从无交际的陌生人联结
从旧照片中定格的陌生人角度来看,当追忆者在社交平台中发布照片以推动寻忆实践开展后,平台的大数据分析技术、算法推荐机制将内容进行传播、推广,促成记忆的“媒介化流动”。其以追忆者为定点(fixedpoint),流动的朝向既可能是其他网友,也可能是被追忆的当事人。对于后者而言,全新的故事也在彼此“相遇”(encounter)的那一刻产生。
我是2月26日的晚上躺床上无意间刷到夏望那条寻人启事的视频,看到那件绿衣服就认出了是自己小时候……第二天一早就去姑姑家找到了当年的照片,下午发了抖音。刚开始信息量也不大,也担心夏望看不到,到了晚上人就多了起来,很多人艾特她……不敢相信……19年了,再次相遇……(ID:AndyMa)
网友的“奔走相告”与算法的“精准推荐”促成了追忆者与被追忆者在媒介空间中“陌生人的相遇”(strangeencounter)(Jackson,Harris&Valentine,2017)。“天哪,中国14亿人,靠抖音找到了彼此。”(ID:悲伤小羊羔)“就好像大数据把所有人连成了一个圈,十多年前的一次擦肩而过都可以在大数据时代找到彼此,这在以前手写信件的时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吧!”(ID:1124753098)对于这些成功寻忆的实践者而言,多年前定格在旧照片中的缘愫如今在社交平台、算法、网友等“人-物”的联结中得到接续,全新的交往与关系也因此得以建立。
(二)续写新记忆:与熟悉的陌生人“重新联结”
记忆一直被刻板地视为已完成的(complete)、残留的(residual),或者不断衰败(indecline)之物(Hoskins,2011b),但在联结转向中,记忆始终保持活跃与“再生产”状态。记忆的生产总是以关系为起点,人类相遇的时刻便是记忆产生的时刻(Hoskins,2011b),这一时刻又为今后的重逢、重新联结奠定了基础,以“陌生”为表征的关系意涵也在彼此互动、旧记忆的唤醒与新记忆的生成中得到了全新解释。
二年级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们在花坛上拍了一张合照……二年级之后我就去外地了,因为没有手机,从此跟他再也没有了联系。没想到居然通过网络的力量找到了他。说实话还是有点紧张的,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相互也不熟悉了。但还好我们都比较注重缘分,所以也一直保持着联系……但我们现在又成为了好朋友,会经常聊微信、打游戏,而且只要过年回老家就会聚在一起。(F11,2023年9月7日)她说很感谢这么多年过去还能记得她,现在已加上小绿继续保持联络。(ID:夹心_III)
对于那些失联许久的人而言,人的主动性和数字媒介的可获取性、便携性以及普遍性共同造就了与“过往”、与“故人”的重新联结,这种因记忆实践而生的联结性既帮助他们重温了已逝的过往(Hoskins,2011b),也在推动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同时续写了全新的交往记忆。
尽管实践中存在质疑的声音——“我不理解,又不是存在恩情”(ID:为你写诗)——但是记忆并不纯粹是功利性产物,人们也清楚地知晓在记忆过度饱和、泛滥的当下哪些记忆值得被召回,“对我们应该记住什么和不应该记住什么的道德判断取决于相应的场合和实践,或者说语境,以及那些能够在提升生命活力、能力和情态(modalities)的过程中帮助我们与其他人相互联结、共同记忆的内容”(Brown&Reavey,2014)。“很多事情无关功利,只是一份情怀,一种内心的感觉”(ID:月弯弯)“不管什么结局,也是一个浪漫的故事”(ID:怀沙)因此,无论是已存的(actual)联结关系,还是想象的(imagined)、有待联结的(potential)关系都具有独特的存在价值。对于那些还未获得“音讯”的追忆者而言,他们过去的记忆在联结行动中也一直处在进行时态。除了网友的联结性见证与帮助,博主“DawnSoon”寻忆陌生人的故事还得到了“沈阳晚报”的报道(沈阳晚报,2023),媒体力量的融入进一步推动着这场于2023年3月12日开启的数字记忆实践的持续进行。这些记忆与实践行动在网络中没有尽头,不会结束,不会遵循线性规则发展(Ernst,2006:110),记忆会在联结中永放光彩。
五、不可忽视的“无法联结”
记忆存储于媒介空间之中,空间的存在又在时间维度为记忆带来了连续性(郑一卉,胡康,2024)。不过,记忆作为“过去”的痕迹与“当下’之间必然存在客观时间层面的距离,如是,记忆在空间中的抽离成为个体在生活中所面对的常态化问题。对此,许多声音将这一问题归结于外部的客观因素,如时间的消磨(Ricker,Vergauwe&Cowan,2016)。然而,本研究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记忆主体决定的。虽然时间的推移确实会消磨记忆的痕迹,但这却不影响记忆主体选择其他媒介方式对记忆进行巩固或重新联结,换言之,主体完全具有影响记忆效果的主动权,如:是否主动存储了记忆内容、是否删除了可以激活记忆的媒介文本等等。尤其对于那些断联许久的熟悉的陌生人而言,他们并非是主动离开了追忆者的记忆空间,而是在时间长河中经历了“被放逐”。在此意义中,被追忆的他们处于时空层面被支配的一方。

电影《陌生人的慰藉》(TheComfortofStrangers,1990)剧照。
不过,当追忆者开始主动寻找被追忆者,被追忆者的时空权力与能动性便得到了体现:他们可以决定是否与追忆者产生联系、是否愿意与追忆者生产新的记忆、什么时候对追忆者作出回应。质言之,追忆者需要完全接受被追忆者的时空节奏(Gasparini,1995),这也使得“寻忆”成为一个“未知的”“不确定的”动态过程,没有人能够保证其结果如何,或何时才能抵达追忆者心中满意的终点。“他刷到了可能也就一笑而过吧”(ID:85后)“就算看见,估计也不会回应你”(ID:可乐)陌生人是一种空间关系的存在(Marotta,2012),被追忆对象在空间中是来去自由的,可以流动、可以停滞,这是他们空间权力的具体表现。如上文的联结情况,被追忆对象可以选择回应追忆者,再次进入追忆者的记忆空间,甚至与追忆者一起开拓新的记忆增长点。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回避,拒绝与追忆者(的空间)产生关联。结果是,在追忆者过去的记忆空间中被支配的这群人恢复了空间的主体性与战术性,回应追忆者的方式成为意义争夺的空间化表现(张杰,2016)。
当然,对于这样的情况,追忆者也有相应的方式进行应对。他们可以永远保留对被追忆方的回忆,永远选择在空间中找寻与等待。虽然找寻与等待的结果是未知的,但它们却是生产共享性、“实现‘集体构想的未来’的一种积极尝试”(Kwon,2015),是追忆者在当下尝试抵抗时间与遗忘(oblivion)的真实写照,虚幻的“可能性”也在此过程中被转化为实际效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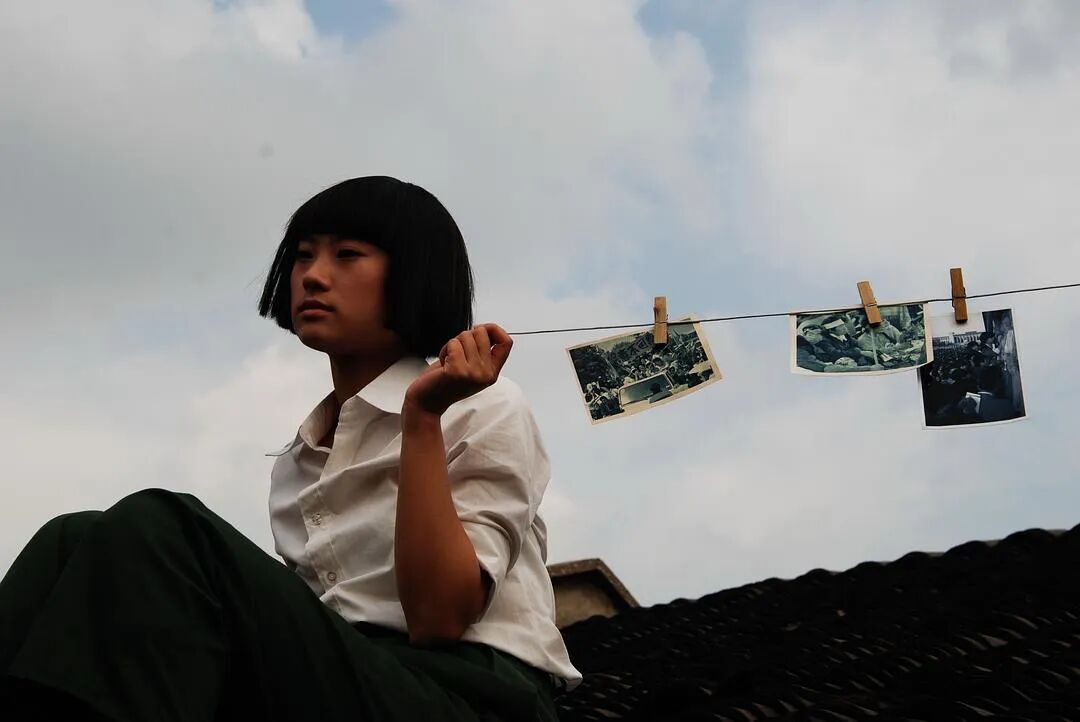
电影《黑白照片》(2010)剧照。
此外,无法联结的情况还启示我们,人际联结中的“陌生与否”已然无法用“陌生”“不陌生”“熟悉”“不熟悉”这些二元互反的词进行粗暴式判定。联结关系本是一种极具张力的“状态”,即使双方之前对彼此知根知底,但这并不意味着多年重逢之后便依旧熟悉。联结的缺位会在双方之间制造出一定的叙事空白区,双方只能在后期重逢并重新联结后对这个区域进行填补。
绝大多数的寻忆陌生人实践都带有“幻想”或“浪漫主义”色彩,追忆者认为过去的美好回忆将成为构筑双方当下关系的基础,“毕竟我们之前有那么多回忆”(F11,2023年9月7日)。这是一种“预媒介化”,即追忆者试图凭借过往的回忆来想象、乃至塑造未来(霍斯金斯,李红涛,2015)。但是,幻想的实现还是破灭却不是一方能够单向控制的。博主“XKJ”在十多年后通过媒介的力量再次联系上了那个陌生人。但事与愿违,“XKJ”说对方“不愿再提起这段往事”。
从博主发给研究者的双方聊天记录截图来看,两人在加上好友后,对方表示,“你想跟我表达什么呢?告诉你这是10多年的照片了,做人踏实点,我这个阅历的人不是你能了解的!”威廉·吉布森(WilliamGibson)认为,有些人知道“如何看待过去”,但却无法“以过去的身份看待过去”(Claire,2014)。对于“XKJ”而言,即使与对方相隔十几年没有联结,但他却一直认为双方过去共同的相处经历仍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彼此的记忆深处,是在当下召唤彼此联结的动力之源。
不过,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似乎并不像物和物相连那样简单,“加上好友”“有了联络”只是联结的基础,其还需进一步考虑到人自身的主观因素,如情感、态度、性格、经历等,或者说,双方是否都能够或都愿意“真诚以待”“再续前缘”才是实现联结的关键条件。尽管“XKJ”和被追忆者在网络、社交平台的示能(affordance)中再次产生联络,但于被追忆者而言,“XKJ”的尝试联结是一种“强制性的联结”,因为在被追忆者眼中,过去仅代表了一个“已经完成的记忆”,而不是“未完成的联结关系”。由此可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可)联结程度”“记忆与人的(可)联结程度”才是较为合理的判断“陌生与否”的依据。
六、未尽的结语
自吉姆·戈梅尔(JimGemmell)推出“我的数字生活”(MyLifeBits)项目以推动“全面记忆”以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聚焦个体记忆的摄录,这无疑助长了记忆热潮规模的扩张。但是,全面记忆的美好愿景背后仍存在大量记忆的断裂之处,由于存在主观层面“生理功能的退化”和客观层面“时间过去已久”等问题,并不是所有人能够实现记忆的“完全召回”(totalrecall)。皮埃尔·诺拉(PierreNora)(1989)也指出,尽管媒介中装满了过往的痕迹,但这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其仍然需要后期的不断追忆。不过,在“人—人”“人—物”的相互联结中,记忆的断裂之处得到了弥合的机会。
互联网和社交平台的发展使得分隔于各个角落的人拥有了彼此联结的契机,所有接入赛博空间的个体都可以充当其中的一个节点,并在与其他节点的联结中编织出巨大的动态交互网络。更重要的是,这一交互网络会随着后续节点的加入或退出而产生“变形”,这既为新的记忆叙事奠定了基础,也为旧记忆和陌生人的成功搜寻提供了可能。
本文所探讨的“寻忆陌生人”记忆实践与“联结记忆”理论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正是借助对该记忆实践的分析使得我们跳出了过去将记忆视为静固或破碎之物的框限。在社交平台铺就的联结轨迹中,追忆者与被追忆的陌生人之间因旧照片、大数据、算法、网友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而获得了彼此联结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联结后的他们并未结束这一记忆实践,而是选择基于旧的记忆建立新的关系、续写新的故事,而那些处于等待联结的记忆仍然在平台技术机制和网友的积极互动中持续向外发出渴望联结的信号,不断激活着记忆实践主体的这段过往回忆。

电视剧《想见你》(2019)剧照。
无论是陌生人,还是熟悉的陌生人,与他们的联结既是实践主体的意愿所致,也是平台、技术、网友,乃至“缘分/概率”合力的结果。这一实践不仅印证了“过去—当下”的相互联结,而且也延伸了霍斯金斯曾经铺下的这根联结的线,使其成为“过去—当下—未来”,因为从时间性层面来看,实践主体对联结的尝试并不止步于联结“过去”和“当下”,更是希望通过建立关系与续写新的记忆来迎接“未来”。当然,数字媒介时代的联结性并不意味着“记忆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媒介的影响,甚至被媒介决定”(胡康,郑一卉,2024b),真正在记忆延续、记忆阐释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仍然是人自身。就像一张旧照片虽然是记忆的载体,但照片背后鲜活的故事却是人的故事,也需要人来讲述。
此外,在利用寻忆陌生人实践来验证联结记忆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仅存在联结的情况,“无法联结”亦会发生,这似乎与霍斯金斯所描绘的情景有所不同。对于霍斯金斯而言,因数字媒介技术的加持,“联结”已经成为普遍的、稳定的状态。但是,在记忆实践中,技术并非主导(李红涛,杨蕊馨,2022),关键仍在于人的“主体性”和“意愿性”。“寻忆陌生人”记忆实践表明,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实现记忆与关系的重新联结,联结或尝试联结的过程亦不是稳定的。
无论是抖音,还是小红书,展开“寻忆陌生人”实践的人不在少数,但除去与陌生网友联结的情况,真正实现与照片中陌生人“联结”的只是少数,被追忆方既可以“按兵不动”,也可以直接“拒绝联结”,这也反向证明了此类记忆实践的特殊性,以及“成功联结”的稀缺性(scarcity)和珍贵性。换言之,并非只有“联结”才具备社会文化意义,那些“无法联结”也并非削弱“联结”的消极存在,正是因为“无法联结”的存在才反向突显出联结的意义与价值,帮助我们更好地发掘联结所需要的条件。而且,“无法联结”同样说明“联结”或“尝试联结”本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并不像霍斯金斯说的那样稳定,而是充满了变动的可能。透过“无法联结”我们也可以发现,追忆者寻找的也许不只是那个人,而更多时候是过去的自己和已逝的青春。
因此,当“记忆找寻”成为主线,反而突出了寻找本身的价值与意义,这亦是主体在当下基于过往所展开的一种记忆书写行动。诚然,“连接转向的论断不应该变成终点,而应该只是一个起点”(李红涛,2022)。本文对于“无法联结”的分析为原有的“联结记忆”的学理内容带来了补充性思考,这将是一个新的出发点。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真理永远在形成的过程中,对于理论而言亦是如此。本文所关注的“寻忆陌生人”极具微光特质,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者可以基于“无法联结的记忆”,从交叉学科的视野探讨数字时代其他宏观或微观记忆的断裂问题。例如,第一,除了因缺乏相应文献或见证人而导致历史记忆的断裂,数字时代算法带来的记忆选择性也可能造成一些历史记忆的边缘化。第二,因情感隔阂或亲人已逝而建构失败的家族记忆。以不同记忆实践案例对“无法联结的记忆”进行类型化分析,挖掘背后的技术因素、情感因素、社会因素、时代因素等,进一步丰富“无法联结的记忆”的学理意涵,这不仅有助于理论验证、否思,而且可以反向突显、增强“联结记忆”的价值,以健康的理论生态促进相关理论的共同发展。
最后,我们需要警惕这一联结记忆实践背后“记忆伦理”问题的发生。追忆者在未获得被追忆对象的允许下,将双方的“合照”单方面上传至网络当中,这必然会引发隐私的泄露问题,也反映出一种悖论:看见寻人启事中照片的陌生网友对寻人信息的进一步传播,知晓相应信息的网友在评论区对信息(如姓名、所在城市、社交账号)的公开成为追忆者“顺藤摸瓜”、成功找寻的关键,因为缺乏这些信息,几乎很难在网络的海洋中进行“捞人”。不过,博主的“怀旧”、网友的“热心”却可能造成被追忆方的困扰。因此,诸如“F5”和博主“夹心_III”最后选择以“停更”“删帖”和私下交往的方式来阻断对方隐私的传播。可见,在此类记忆实践中,“记忆伦理”中的“记忆权”与“被记忆权”亦是未来值得探讨的角度之一(李红涛,2024b;玛格丽特,2015)。
[文献出处]胡康、郑一卉:《寻忆陌生人:数字记忆实践中的“联结”与“无法联结”》,《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6期,页119-136。
作者/胡康(安庆师范大学传媒学院讲师)、郑一卉(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本期评议/黄典林(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
文本摘选/罗东
导语校对/薛京宁
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请发送邮件至 203304862@qq.com
本文链接:https://jinnalai.com/jingyan/78121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