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谢宇弑母案自2016年暴露以来,在坊间引发强烈且持久的反响,案件的每一点进展,如凶手2019年被抓捕归案、2021年一审被判死刑、2022年原定的二审因故推迟、2023年二审维持原判,都引发一波波的关注和跟踪。绝大部分舆论都不约而同地有一种猎奇的心态:吴谢宇为什么弑母?其弑母的直接动因是什么?他何以从“宇神”和母亲的“小棉袄”蜕变为残忍的弑母者?
在吴谢宇案的所有报道中,《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第29期发表的《吴谢宇:人性的深渊》,无疑是最全面、系统和深入的。该报道共计九章,近十万字。今年5月,该报道单独成书,又增加了对吴谢宇逃亡期间结识的女友的采访。本文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肖瑛围绕该书撰写的评论,节选自《人性的深渊:吴谢宇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小标题为编辑所加,注释从略。
报道吴谢宇案的价值
在有关吴谢宇案的讨论中,媒体特别是自媒体各显神通,充分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做出了层出不穷的解释,其中最流行的是想象空间无穷大的性本能机制,然后是心理学机制,譬如很多报道强调吴谢宇虽然为人很好,但很少跟人“交心”,有的报道甚至将之归罪于“激情杀人”,譬如一篇后来在网上再也找不到原文的报道的标题就暗示:吴谢宇同其母亲的某次口角是其弑母的直接动因。当然,也有从学校教育缺位和原生家庭畸形等角度展开分析的。
但所有上述分析都是猜测。因为从媒体和自媒体披露的信息看,这些分析无一例外地缺失一个促使吴谢宇从大一大二的优秀、阳光男孩转向大三的逃学、缺考并最终回家弑母的转折点,也缺乏一个吴谢宇将弑母冲动转化为将近半年的策划然后在2015年7月10日决定付诸行动的直接原因。按照常理,大三期间,吴谢宇身上一定发生过对他而言具有根本冲击性的事件,让他对大学生活以及未来人生失去信心,抑或让他将所有问题归罪于他的母亲,抑或如他自己所述的,因爱而弑母,帮助母亲脱离苦海。可惜,除部分司法人员有机会同吴谢宇直接接触外,记者、学者、吴谢宇的亲人都没有机会(或回避)直接与作为杀人犯的吴谢宇深入交流,而其自述和信件的“道德自净”痕迹太过明显,让人不仅难以采信其解释,反而觉得他是处心积虑地掩盖弑母的真正缘由。吴谢宇弑母的直接动因,估计要被他永久地带入坟墓了。
《人性的深渊》这篇报道的作者吴琪和王珊,围绕家庭、友人、学校、法庭这四个与吴谢宇及其核心家庭最为密切的社会关系网络,从2019年开始,先后联系了上百位同吴谢宇有关的人士,对其中愿意接受采访的人士做了一次甚至多次访谈,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并借助吴谢宇的狱中自述、书信、法庭供词等,系统梳理了吴谢宇及其父母的生命轨迹,努力还原吴谢宇走向弑母深渊的过程。由于没能直接从吴谢宇那里获得关于其大三生活中发生的根本性地影响其人生态度甚而策划和实践弑母的具体原因,所以,两位记者在报道中没有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为谋为吴谢宇案盖棺定论。但是,正因为记者的这种自觉,这篇报道的价值一方面根植于吴谢宇案,另一方面远远超出该案本身,具有极强的社会学味道和深刻的社会反思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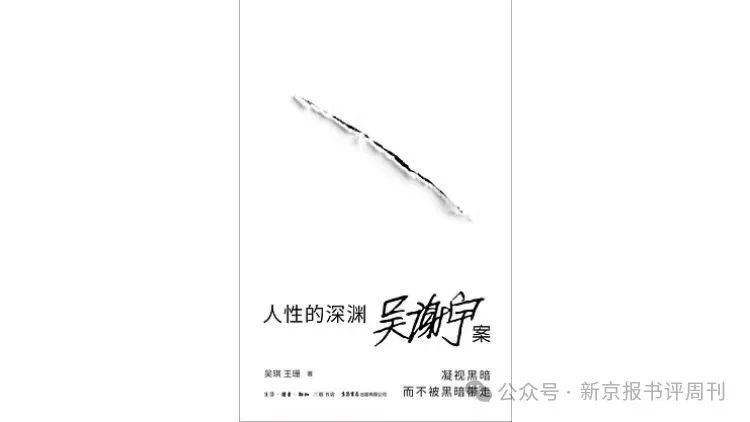
《人性的深渊:吴谢宇案》,作者:吴琪/王珊,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5年5月
从吴谢宇案本身来看,这篇报道深度揭示了吴谢宇所处原生家庭的特殊性及其形成原因。作者不满足于仅通过案发时谢天琴、吴谢宇的核心家庭的结构和情感状况来呈现吴谢宇所处的社会情境,而是引入家谱视角,追溯吴谢宇的祖父辈甚至更前一辈的家庭构成,清晰地呈现了吴家和谢家更为悠长的家族史。报道一方面描摹了吴志坚和谢天琴两位性格完全不同、家庭条件相异的大学毕业生是如何走到一起结为连理的,细致描写了这对夫妻各自的性格和彼此关系,给读者绘制了一幅福州城中一个既普通不过又有其独特个性的三口之家图画;另一方面对吴志坚和谢天琴特别是后者的家庭史探幽析微,时代的政治动荡落在谢父头上,意义就不同了,不仅影响了谢父的个人命运和家庭状况,也可能塑造了谢天琴和她的妹妹、弟弟们的性格。谢父的“右派”身份和谢父谢母双盲的现实,决定了谢家在当时还是弹丸之地的仙游县城必然处于社会的底层和边缘,谢天琴从记事起就可能被同学、邻居的各种嘲笑和奚落所包围,虽然嘲笑者和奚落者并不一定带有恶意,甚至也不明白谢父身上标签的实际意涵,但他们的欺负肯定在排行老大的谢天琴的心中切割出一道道血痕。她要保护父母,要保护自己的弟弟妹妹,但她没有能力反抗和回击。到了上学年龄,她保护自己的方式增加了一层,那就是取得好成绩,换来同学和老师的认可。
在这样憋屈的环境中,谢天琴不由自主地形塑出对外警惕、自我封闭、高度自立和要强的性格,同时可能还潜伏着缺爱的隐痛。到20世纪80年代初,谢父的“右派”身份得以改正,家庭经济条件好转,但谢天琴估计已经很难抹平童年的创伤。大学毕业后,谢天琴偶然结识了吴志坚,并在其身上发现了爱情,也找到了依靠,然后全身心地投入(读到谢天琴时,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李安电影《饮食男女》中的朱家珍,她们两个先是不相信爱,但渴望爱,一旦获得爱,就奋不顾身地去拥抱)。但是,吴志坚的父母家庭以及他的性格和工作,都决定了谢天琴没法守护好这个小城堡。

电影《饮食男女》剧照。
“苦难的共同体”
虽然“原生家庭说”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但是,当把吴谢宇的家族史和核心家庭以及教育放到显微镜下来打量时,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这个家庭的特殊性和罕见性。但即使是这类家庭,也不必然发生弑母弑父悲剧。从这个角度看,聚焦于原生家庭,虽然可能给解释吴谢宇案提供一条常识化的线索,但相对于吴谢宇自己的真正心理动机,这个线索仍然是外部的和特殊的。而且,当我们每个人都由此而将自己身上的不幸归因到原生家庭时,其实可能催生出反家庭的偏见。
由此可见,对吴谢宇案的社会意义上的解读,或者说对吴琪和王珊两位记者对吴谢宇案的报道的社会意义上的解读,还需要有进一步的跳脱。跳脱的机会,存在于《吴谢宇:人性的深渊》的读者对吴谢宇或谢天琴不由自主滋生的某种“代入感”上,他们在这对母子身上,多多少少发现了自己的影子。从这个角度看,《吴谢宇:人性的深渊》,恰恰在两位记者高度细致和特殊的描述背后,有意无意地触碰到了当代中国人在家庭生活中遭遇的普遍困境。吴志坚和谢天琴自己的生活并不宽裕却必须将很多资源反哺大家庭的无奈感和牺牲感,等等,都可以在现实的饮食男女身上找到或多或少、或浓或淡的痕迹。因之可以说,吴谢宇案是非典型的,因为弑母毕竟是极为罕见的人间惨剧,但吴谢宇和谢天琴甚至吴志坚的困境是普遍的,故而吴谢宇案又是典型的。
这些普遍的“代入感”,不只是源于具体的原生家庭,更可能源于时代变迁对家庭的深刻再造。我们这些在改革开放之前就能记事、在大家庭中出生和长大、在城市中组建自己的核心家庭并为人父为人母的中年人,对家庭结构和家庭生活的前后变化肯定有着诸多的共同记忆。这些变化,与其说是个人奋斗使然,毋宁说是时代锻造的结果。
我称传统农业社会下一些大家庭为“苦难的共同体”。共同体是玫瑰色的,表达的是情感、伦理、生活上的相互理解和支持,相互无功利的关爱和抚慰,唯有守望相助、惺惺相惜的幸福,而无你争我斗的苦难和欲罢不能的纠结。共同体的理想形态是“家”。但是,现实中的大家庭对生活其中的人来说,并不只是玫瑰色的,而往往与苦难相伴。一方面,每个家庭都有不言而喻的中心,如包括父亲和长子在内的男性,有理所当然的目标,如存续和传承。围绕家庭的中心和目标,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放弃自己的个体性和欲望,作为家庭之“一员”而无声地任劳任怨。这样的家庭,其“共同体”面向遮蔽了其“苦难”面向。这类家庭,不能说是消灭了“苦难”,只能说家庭成员的“忍”让“苦难”潜伏了。另一方面,很少有家庭的所有成员能始终如一地自我克制、自我奉献,总有成员会“忍不住”暴露一些私欲和个性,总有成员质疑家庭内部的分工和分配的“不平等”。于是,在外人看来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却可能让一个家庭鸡犬不宁。此时,“苦难”替代“共同体”成为理解和反观家庭生活的主要角度。其实,在大家庭中,苦难和共同体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是大家庭构成和维系不可或缺的一体两面:没有个人依赖共同体而活的内在需求,苦难对他们而言就无法忍受;没有对压抑个性和欲望的苦难的忍受,共同体就难以维续。

电影《隐入尘烟》剧照。
如何既降低“苦难”又维续“共同体”?前人的智慧是“分家”和“反馈模式”的相互支持。当然,要同时保全这二者,前提是农业社会。在农业社会下,经济资源有限,人口流动性较低,故而“分而不离”是“分家”的普遍特征:“分家”后父母的家庭与子女的家庭、兄弟之间的家庭,仍然比邻而居,低头不见抬头见。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社会继替”目标的实现,在西方主要依靠“接力模式”,每一代长大之后自然地离家出走、成家立业,故而每个家庭都只是接力棒中的一个临时性节点,但在中国,除了“接力模式”,还有更为重要的“反馈模式”。
如果说“接力模式”要求每一代人在年幼时履行子女职责、成年后履行父母职责,其继替线索总体上看是单向的、线性的,那么“反馈模式”则是以家为中心的,子女的价值在于“尊祖敬宗和家族绵续”,在亲代跟前履行好“子女”的职责,其继替线索虽然总体上向前绵延,但每个节点都要往返。换言之,在中国,子女不仅要学会长大后“做父母”,同时要学会“做子女”,承担“为人子女”和“为人父母”的双重任务,并且“为人子女”角色是“为人父母”角色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双重角色的习得都依赖于现实家庭生活中周而复始的耳濡目染。但是,核心家庭只能为“接力模式”提供学习机会,却无法实现“反馈模式”的教育与体验,只有在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中,在同时存在多个三代同堂大家庭的邻里环境中,才有机会接受如何以“做子女”来践行“做父母”职责的日用而不知的熏陶。
一句话,“长大之后我就成了你”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身处其中的人可能无法挖掘和解读各种家庭角色所蕴含的情感和伦理意涵,但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扮演什么角色、履行什么职责,却是水到渠成、不由分说的。这样,“身教”之下,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有效克制甚或消除自己的私欲,但一定很难生长出自杀或者弑母弑父的想法和举动。
在如此尚未充分开化的大家庭中,“社会继替”的“身教”一定是总体性的,其核心是引导人如何“为人子女”和“为人父母”。支持这两种家庭角色的基础只有“孝道”,孝道构成大家庭和整个社会的总体性知识,当然也是其总体性伦理。除此之外,其他的困惑如青春期、性苦恼等,都尚未进入家庭和社会的文化词典,不可能成为“为人子女”和“为人父母”的内涵,当然也就不可能以这些有关养育的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作为衡量和判断“为人父母”的好坏和是否合格的标准了。
转型社会中家庭的“纠结”
改革开放为城市化和流动化注入了强劲动力,中国社会迅速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从自然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家庭,在这个过程中无可奈何地承接所有这些变迁带来的动力和压力。一方面,农村人通过各种途径在城里立业、安家;另一方面,虽然传统家庭的“苦难”因少子化核心家庭中家庭关系的简化而减弱,但核心家庭的新困境也因此而凸显。对于在农业社会大家庭氛围中成长、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城市组建核心家庭和养育子女的中年人群如吴志坚、谢天琴来说,由此很难不滋生出各种前所未有的“纠结”(ambivalence)来。
首先,核心家庭的自我定位模糊化。如前所述,农业社会中家庭的存在价值和目的是自然而然、不言而喻的,所有家庭都会醉心于自己的维系和绵延,有望族味道的家庭在此之上会添加光宗耀祖、家庭地位提升的目标。但是,现代核心家庭的定位遭遇了普遍挑战:家族绵延和光宗耀祖肯定属于“封建”性质;养儿防老的说法很流行,但暴露了父母一辈的自私;是因为爱而生育和养育吗?似乎有些“言不由衷”;对子女的无条件投入是以人力资本投资来换得父母的自我价值实现感吗?在资本“残忍”的语境下,也被涂抹上制造“韭菜”的不正当感。总之,在各种意识形态的挑战下,“为人父母”本身就成了问题,其正当性基础摇摇欲坠了。这类质疑,直观地看是让父母在子女面前变得无所适从,更深层次地看,其后果也会落在质疑者即子女自己身上,对生命的珍惜,对社会化的接受,对社会继替责任的承担,现在都成了他们反思家庭和自我的对象,“社会继替”在很多家庭中变得难以“继替”。以吴谢宇为例,虽然他在给亲戚和友人的信中口口声声倾诉着自己对父母的爱,但其弑母和骗取亲戚及父亲友人的金钱的举动,就很难让人相信他有捍卫家庭正当性的意识。
其次,家庭面对专业知识涌入无所适从。过去四十多年来,无穷无尽的福柯意义上的“人的科学”(humansciences)进入家庭。传统的“育儿”和“教育”模式不再有效,合格的父母一定是掌握并能熟练运用各种相关专业知识的父母。在专业知识的指挥棒下,很多家庭因为在如何育儿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而制造出大量的代际矛盾:一方面,年轻的爸爸妈妈需要依赖上一辈来帮助自己养儿育女,另一方面又对上一辈的养育模式大加挞伐。问题在于,诚心实意地亦步亦趋追随各种专业知识的家长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些知识?答案至少不是完全肯定的,因为在这些知识的使用中,如何做到恰如其分、防止物极必反,就让一般人倍感踌躇。譬如,对青春期的子女进行性教育,如何既破除生理方面的神秘感,又避免在子女脑海中播下淫秽的种子?爱的教育,如何既让子女体味父母自然的爱,又防止放纵和溺爱?等等。这些,对于在传统家庭中成长起来的父母而言,是很难掌握并身体力行的能力,虽然他们可能在某些专业领域掌握了精深的知识和技术。正因为如此,吴志坚没法向吴谢宇解释自己电脑中的“小资源”,没法以此为机会给吴谢宇适当的性教育,也没法解释他与另一个女性的关系,他唯一的应对办法就是像瓦依那乐队那首《大梦》所唱的,“我的父亲总沉默无语”,或者干脆装作视而不见。

电影《隐入尘烟》剧照。
复次,家庭功能出现社会化和伪社会化的矛盾。相比于传统,今天的家庭一方面是功能的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是功能的分解和社会化,如养育、教育、福利、职业,都被不同的社会专业机构所接纳。总之,传统家庭的总体性特征被一步步削弱了。但是,家庭仍然是最基本的社会组织,难以摆脱其初级群体的位置,被专业机构所添加和承接的功能仍需要家庭的接应,譬如孩子最好的老师还是父母,学校教育的抽象性需要在家庭生活中具象化,否则对孩子而言永远是抽象的教条。更为严重的是,家庭功能的社会化还在流于形式,实质的社会化在很多方面尚付阙如。譬如养老,至少目前我们社会整体的职业伦理状况使很多家庭和老人对社会化养老望而却步。在教育上,大部分学校似乎并没有实践其所宣称的伦理和情感教育功能,为人的教育,包括尊重他人、将心比心的能力,在现实的学校教育中是无法想象和实践的,学校实际上只是将自己定位为传授最可操作和最容易传授的知识,即使伦理、情感和生理教育,唯当转化为试卷和分数后才能在学校教育中找到落脚点。一言以蔽之,学校教育主要是应试教育和专业教育,或者更为直接地说是“卷”的教育。不只如此,学校还将“卷”的紧张感植入家庭,“绑架”家长,逼迫家长不得不拼命地迎合之。吴谢宇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教育的典型,“成绩好”是学校和家长对他共同的也是唯一的要求。这可以被理解为家庭教育功能的社会化未能取得成功的体现。

纪录片《高考》剧照。
但是,在当代既分且离的核心家庭中,父母即使有心,也无以全面承担起对社会人而言不可或缺但学校无意承担的为人教育了。相较于“分而不离”的大家庭为“反馈模式”和“接力模式”的“身教”提供了条件,当代核心家庭之间空间距离遥远,就如吴志坚和谢天琴各自的父母之家与他们在福州的小家之间的距离。在两代人的核心家庭特别是独子的核心家庭中,无论是哪一代人,扮演的角色都是单面的,父母只是“父母”,无以同时为“子女”,子女只是子女,无以同时为“父母”。而且,因为只有两代,核心家庭的重心必定是子女,子女是家庭的本位。即使吴志坚和谢天琴依然实践着他们从小耳濡目染的“反馈模式”,赡养或者帮助着远在老家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吴志坚去世后,谢天琴又接过了亡夫的这副担子,但是,他们扮演的“子女”和“兄长”“姐姐”的角色,对吴谢宇而言是抽象的,是不可见的。“吴谢宇们”除了相信自己是家庭的核心,整个家庭都围着自己转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再也不能有关于自己在家庭中的其他角色和位置的想象,更难以培育“反馈模式”中如何做好“子女”以及如何扮演家庭其他角色的道德和情感自觉。
我们姑且相信吴谢宇的自述和信件的内容确为其真实心声,那么,他将其母亲“生不如死”的叹息“直男”式地解读为真的想弃世而去,从而因爱母而弑母,痛恨父母的兄弟姐妹和朋友对他们母子俩不管不顾从而在弑母后从他们那里骗取大量金钱,甚至在“借钱”屡试不爽时,也未能感受到这些亲友对他们母子的真诚牵挂和关爱,就恰恰说明在他的家庭中,缺乏“反馈模式”的“身教”,缺乏超越自我主义的多重家庭角色的观摩、想象和扮演经历。吴谢宇身上体现的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不只是他个人的尴尬,也是当代很多核心家庭的尴尬,不只是他个人或其父母的责任,更是当代大部分核心家庭的普遍困境使然。在这样的家庭结构中,他们需要做的只是尽情汲取父母养育他们的红利,却未曾有机会去体察和实践“反馈模式”中的“子女”角色。更有甚者,一些子辈从父母对他们的含辛茹苦中,感受到的只是“为人父母”之艰辛,果断地决定不重复父母的老路,从而切断了自己“社会继替”的责任,家庭由此而终结。
重申前面的观点:没有几个家庭会出现吴谢宇案的悲剧,因此,这个案件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个案;吴谢宇案也是今天中国一些家庭面对的各种困境的极致化表达,因此,它又具有某种意义。
如何面对这种困境?当然不是简单地在传统家庭与现代家庭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重回传统。传统永远回不去,也不值得全盘回归,在个体意识已经勃兴的背景下,很少有人会为了习得“反馈模式”中的不同家庭角色而甘愿承受自我牺牲和复杂家庭关系潜藏的“苦难”。
跳出吴谢宇案来反观吴谢宇案,对我们而言,有三重意义:一是不同时代的家庭有不同性质的纠结;二是当代家庭有其在历史上独特但在当代普遍的纠结,我们就处在这些纠结中;三是我们能做的,是直面这些纠结,积极探索走出纠结的合适道路,期待我们自己也让我们的子孙能够生活在玫瑰色的而非苦难的共同体中。
这正是吴琪和王珊两位记者的工作价值所在。
撰文/肖瑛
编辑/刘亚光
校对/杨许丽
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请发送邮件至 203304862@qq.com
本文链接:https://jinnalai.com/jingyan/75071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