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4月16日,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宣判。
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法官在判决书中写到:“被告人违背被害人意愿,强行发生性关系,构成强奸罪。”在随后公布的《审判长答记者问》中,司法系统发出了清晰的声音,重审了朴素的法律原则——“与妇女发生性行为不能违背其意志,与双方是否订婚没有关系。”
过去两年里,这起强奸案多次登上热搜。其实案情并不复杂,但却因双方的订婚关系、18.8万的彩礼、性同意等议题,被迅速推入舆论漩涡。在复杂的舆论光谱中,受害者及其家庭的贞洁、动机与人格,经历了一次次的残酷审判。
早在2024年初,一场大雪过后,我就曾到过大同阳高县,找到了案件中的两个家庭,到达了案发现场,看到了与之相关的材料,包括视频监控、通话录音、聊天记录、合同文件……试图了解这个案件的全部细节。
被卷入的双方,观念不同、立场不同,但不得不面对一些共同的问题:亲密关系里的性同意和性暴力,究竟是怎么回事?对这两个条件普通甚至是贫穷的家庭来说,彩礼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们看待性的观念如此不同?以及,对受害者来说,要怎么结束这一切。
文 |林松果
编辑 |姚璐
运营|起泡菌
图|(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提供
3小时
2023年5月2日下午3点,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一对年轻男女走进了县城里一栋居民楼。
对阳高县居民来说,这是一年中最宜人的季节。这里与内蒙古接壤,北风劲吹,冬季漫长,土壤封冻。但这天气温在11度到27度之间,不冷不热,正值五一假期,县城比往日热闹。
下午3:05,电梯监控记录了他们停留的一分钟:女生长发,绑马尾,穿一件黑色短袖,男生穿白色衬衣,戴眼镜。女生穿的短袖是奥特曼的图案,拍一拍会发光,她拍了一下,灯亮了,身边的男生也伸手拍了一下。接着,男生抱住了女生。女生有没有回应,视频里看不清楚。14层到了,他们出了电梯。
他们再出现在电梯里,是3小时以后。下午6点左右,他们在13层上了电梯,又在14层下去——女生是被男生拽着的,她看起来情绪不太好,想挣脱,想往地上坐。第二天她母亲拍摄的照片显示,因为拖拽过于用力,女生的胳膊留下了淤青,有清晰的手指印。
电梯一进一出,两段视频,两人的关系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他们本是刚订婚的情侣,男生27岁,女生24岁。前一天办完订婚宴,案发当天的午饭,也是两家一起吃的,按照大同风俗,女方回请男方,叫“请女婿”。吃完午饭,他们进入的房子,是男方准备的婚房。但就在当晚10点52分,女生报警,电话里她说,自己被男生强奸了。
房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公安局做笔录时,双方陈述了各自的版本——他们到达房间后,因为忙订婚太累,两人睡了午觉。5点左右,男生提出发生性关系。至此,说法出现分歧。
女生说,她拒绝了这个提议。他们之前约定过,拒绝婚前性行为。为了抵抗对方,她躲到房间榻榻米的角落,对方抢走了她手上的被子;她大喊大叫、踢衣柜,男生让她别叫;她躲到窗帘后面,男生一把揪下了窗帘。强行发生性关系后,她想走,男生不让,她为此点燃了房间的柜子、客厅的窗帘。男生去检查火的时候,她跑出房门。电梯不来,她就从消防楼梯往下跑,刚跑了一层,男生就追了上来,“我大喊救命,但是没有人理”。
但男生说,女生当时没有任何抵抗。至于点火、逃跑,是她事后情绪不稳定。
之后,警方进入房间,搜集了一些证据:除了女生的身体检查结果、手臂淤青、证人证言外,他们还提取了电梯监控、案发时的床单(检出了两人的DNA)。客厅里有被烧焦的窗帘,卧室里也有被扯掉的窗帘,房间柜子有被火烧过的痕迹。
几个月后,阳高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男方席某某违背受害人的意志,构成强奸罪,判刑三年。为了回应舆论质疑,阳高县人民法院还发布了一份《答记者问》,法官解释了判决的原因:双方虽已订婚,但女生明确表达过,反对婚前性行为。案发这天,男生还是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虽然事后双方有协商的情节,但不影响认定席某某的行为构成强奸罪。”
法官的讲述,也认定了女生的说法——事后,她情绪激动,实施了点火烧卧室柜子和客厅窗帘等行为,还逃出房间,通过步梯下至13层呼喊救命,后被强行拖拽回房内。
其间,她的手机被拿走,直到回家途中,母亲打来电话,她才重新拿回手机。

很难说清楚,这对情侣对彼此有多少了解——从2023年1月30日相亲,到2023年5月2日案发,他们相识还不足100天。
男生席阳,27岁。他家在阳高县龙泉镇的一个村子里,两间平房,两张大炕,父母种地,种玉米,还养了上百头猪。他有个姐姐,大他好几岁,已经结婚生子。很自然,他一直是家里最受宠的孩子。他母亲甄丽讲,“我们家孩子是老小,家里的事不用他操心,就活得自由自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席阳中专毕业,十几岁就出门打工,在上海待过四年,做地铁安检员。上海房价太贵,留不下来,疫情前,甄丽让他去了北京——离家近,坐高铁就一个多小时。在北京他做过外卖员、快递员,最后一份工作是装修公司的销售。疫情期间工作不好做,存不下钱,爸妈贴补他。2022年底他决定回家,在阳高本地一家大数据公司找到了新工作,做运维,月薪4000元左右,两班倒,公司给交五险一金。
回家了,工作也稳定了,他的婚姻就成了父母最着急的事。早在2017年,他们就在阳高县城给他买了房子,两室一厅,20多万,连装修、买地下室,一共花了40万。2022年,又给他买了一辆车。
他家的话事人是他妈妈甄丽。甄丽短头发,和丈夫浓重的口音不同,她能说普通话,和她打交道,能感觉到她的温和有礼,里头也有强势。甄丽不爱社交,平常埋头在家干活,“不好出门”,所以没人给儿子介绍对象。2022年年底,她找到了县城的一家婚介所,把席阳的资料,交给了媒人孙桃花。
没过多久,孙桃花打电话给甄丽,说有个女孩,“很适合你家儿子”。这个女孩,说的就是朱斐。
朱斐,1999年出生,当时23岁,刚刚大专毕业。她也是阳高县本地人,和妈妈住在县城的平房里。朱斐的相亲资料,也是妈妈递过去的——她年纪小,没想着找对象。这之前,她在太原读书,在山东威海实习过一年,又到太原工作了一阵。2022年底,疫情严重,妈妈让她辞工,回了家。
2024年1月,阳高刚下过雪,气温接近零下20度。来自内蒙古的北风吹过来,带来雪与冰。在朱家院门口,我见到了朱斐的妈妈。她今年62岁,长头发,白发一缕缕。她说,自从“出事”之后,女儿受了刺激,精神不稳定,所以她没办法邀请我进门。我们裹着袄子,站在院子里,在呼出的白汽里说话。

她告诉我,朱斐3岁时,她和前夫离婚,3个儿子归丈夫,女儿归了她,跟她姓。她管得严,女儿从来没谈过恋爱。“我经常教育孩子,咱们到什么年龄,办什么事。咱们是学生,不搞对象”,“她胆子小,怕得不行,就怕遇上渣男”。
等到朱斐大专毕业,朱斐妈妈想法变了——她过了60岁,身体越来越不好,有萎缩性胃炎,睡眠也糟。她想赶紧“给孩子安排个合适家庭”,万一自己哪天有什么闪失,女儿结了婚,她也安心。
2023年1月31日,席阳和朱斐,还有两位母亲,四个人在婚介所见面了。这就是相亲。
在阳高县,婚介所依然是一种挺有市场的婚配方式。除了线下门店,婚介们(通常是女性)也会在抖音、快手开号。介绍席阳和朱斐认识的婚介孙桃花,在快手就有近万个粉丝。她经常在晚上开直播,找对象的男女可以在她的直播间连麦。这也是她们招揽顾客、增加知名度的一种方式。
通过婚介所找对象,对这些没有门路和关系的家庭来说,是一个省心的选择——婚介有一套完备的流程,会在男女相亲的全程提供服务:找对象的男女,交几十元报名费,把资料交到婚介所,婚介就会推荐相亲对象;两人第一次见面,婚介提供场地、茶水;见面后,婚介询问彼此的意见,推进进程;如果男女谈得来,她们就会催促订婚。现在的彩礼重,一旦涉及到钱,为了避免纠纷,婚介还会提供合同,让双方签字。
男多女少依然是一个普遍现象。婚介孙桃花发布的视频可见,征婚的男嘉宾排号排到了590多位,而女嘉宾是200多位。
男女订了婚,婚介才收中介费。席阳和朱斐订婚后,双方都付给了媒人孙桃花1000多元。

钱、情、性
2023年1月30日,这一天的相亲算得上顺利。席阳和朱斐,还有两位母亲,聊了一上午,一起吃了午餐。第二天,席阳邀请朱斐出去玩。之后他们又见了几次面,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
甄丽看得出来,儿子喜欢这个姑娘。之前他也相亲过,但没成功,“(这次)一相就相中了,我还觉得挺好的”。
关系进展得很快。认识第5天,在微信里,席阳向朱斐提到了“订婚”。这也是甄丽的意思,她想,既然两个孩子合得来,她想看看女方家里要多少钱。如果太高,他们接受不了,就及时止损,“不想让我儿子付出这么多”——他去女方家,水果一买就是几百块,还要约会,都花钱。如果真订婚了,这样付出,甄丽能接受。
认识第6天,也就是2023年2月5号,席阳向朱斐提出了一个彩礼的方案,18.8万,包五金。他让朱斐和母亲商量,朱斐表示同意。18.8万这个价钱,在当地算高,但也不算太夸张,为了儿子能结婚,家里咬咬牙掏了。朱斐的母亲也说了,彩礼她不留,婚后会让朱斐带回小家。
但关系进展太快,虽然谈着彩礼,但朱斐也表现出了犹豫和不确信。她大专毕业,觉得在阳高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本打算过完年,就和同学一起去西安工作,票都买好了。她还打算走,意味着这段感情在她心里的分量没那么重。
席阳挽留她,让她留在县城工作,她没有同意。但出发前夜,她母亲拦住了她。母亲的意思是,她既然相亲了,找了个对象,就不要再出门了,留在阳高好好恋爱,在本地找个工作也行。
朱斐最初很难接受,她在微信里跟席阳抱怨,阳高的工作机会少。席阳建议她去做淘宝客服,或者去移动联通营业厅工作。她找到一个招聘信息,发给了席阳,是县城一家公司招聘办公室人员。
交往时,他们呈现出不太一样的爱情观。甄丽说,她儿子比较大男子主义,挑选对象“也很严格”,浓妆艳抹的、穿衣服露肚脐眼的女孩,他不喜欢。他挣得不多,但却说,只要朱斐愿意,她可以不上班,他来养家。甄丽问他,朱斐人怎么样,席阳说的是,“收拾屋子啥的,这方面还行”。朱斐也在微信里问过他,哪个瞬间对自己心动?他说的是,看到朱斐为他整理好卫生间的洗漱用品,他很感动,还拍了照片。但这个答案,朱斐不满意,她说,你娶的是老婆,不是保姆。

性,以及两个人关系的尺度,在他们交往的三个月里,始终没有达成统一。
认识半个月,朱斐就在微信里明确告诉席阳,“咱们也说好,拒绝婚前性行为”,席阳回复了一句,“领证了就是夫妻了啊”,发了三个捂脸的表情。但朱斐的语气很认真,“不出轨,不家暴,不骗我,给我撑伞,别到时候撕烂我的伞”“想好,结婚是很认真的事,别一会一个样”。
朱斐坚定的观念,或许受到了母亲的影响。她妈妈告诉我,她家“家教好”“从来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她认为女人必须保护自己,说得更直接一点,不能有婚前性行为。“你搞对象,你不是女儿身了,别说别人,你自己就(抬不起头)……你要是有孩子了,更羞耻,这咋弄呀?”“咱们还没结婚,不受法律保护,谁能付出那么大的代价?钱(指彩礼)可以退,但是那样(发生性行为)了,能补吗?有孩子了,怀孕了,要是你不要了,我们找谁去呢?”
正因为此,他们交往后不久,有过一次不愉快——朱斐的妈妈要求,他们出去约会可以,但下午6点前必须回家。有一次,席阳接朱斐出去玩,晚上10点才送她回家,她妈妈不高兴。席阳再约,朱斐就不出来了,“你是不是被圈禁了,怎么出不来?”朱斐回复,“还想出来?”“我把我妈微信推你,你问问我妈”。
但男方母亲甄丽,愿意相信另一个版本的故事。案发后,她在网上发帖求助,说席阳与朱斐相识后不久,就去过县城那间空置的婚房,因为她有一次去,看到门口拖鞋的位置动过了,床上有两床被子,床单上有女生的长发。她当时挺高兴,觉得两人感情好,是好事。但后来,她这个说法逐渐演变成“他俩同居过”“他们都在一个被窝里睡过”——案发后,男女双方的笔录都显示,他们此前未发生过性行为。
这3个月里,钱,是双方之间另一个矛盾之源。
席阳与朱斐的聊天记录里,常常谈到钱。认识第一周,他们就在讨论彩礼的价格,当地习俗要给新娘买新衣服,衣服该是多少钱,婚礼时上车、下车又是多少钱,婚戒多少钱……男方应下了18.8万的彩礼。但甄丽说,她家养猪,猪价不稳,收入也有大小年,平均下来一年大概能挣6到10万,这几年花得多,彩礼家里一时拿不出来。订婚时要先给10万,家里没有,她问,能不能先给58000元,朱家不同意。最后甄丽卖了34头猪,又找席阳的姐姐借了3万,凑了10万。
另一个争议是房子。席家为儿子准备的婚房,是席阳单独所有,2023年4月,朱家提出,想在房本上加名字。对这个要求,甄丽不舒服,觉得他们要得太多了,但也不好意思撕破脸,怕婚事黄了。她说,等他们感情稳定了,结婚一年再加名。但女方看来,这个承诺比较虚,他们希望朱斐的未来有个保障。
于是,在5月1日的订婚宴上,双方闹得“不太高兴”——在宴席上,媒人孙桃花拿出已经写好的信纸,一式两份,作为契约,上面写着:席阳本人与父母亲,承诺并同意,席阳与朱斐结婚一年后,房本上加上朱斐的名字。
当时朱斐的大哥也在,看到这张纸上的内容,他指出,“一年后”这个说法不合适,一天也可以是“后”,几年也可以是“后”,他建议,划掉这个“后”字,在结婚一周年当天加名。
两家就这个“后”字掰扯了很长时间。席阳本人倒并不在意,嘻嘻哈哈的,用手机拍了好几段视频。但甄丽不高兴,“当时我就有那个心思,今天别订婚了”。当然她没说出来。他们家每个人都签了字,订婚宴就这样结束了。
接着就是第二天,两家一起吃过午餐,席阳让朱斐陪他去自来水公司,补办家里水表的票据。补完了,他说怕丢了,让朱斐陪他去新房,把发票放下。
下午,强奸案发生。

案发后的24小时,发生了很多事。不仅发生在这对男女之间,真正在博弈的是两个家庭。
朱斐的母亲是最早知道此事的家属。案发后,下午6点51分,她做好了晚饭,纳闷女儿怎么还不回家,给她打电话,过了好一会儿才接,一接通,那边“哭得撕心裂肺”,朱斐说:“妈,我被席阳给强暴了。”妈妈安慰女儿,“不要哭,不要着急,回来再说”。
阳高县人民法院在那份《答记者问》里提到过,席阳拿走了朱斐的手机。我查阅了多份强奸案的判决书,是否拿走受害者的手机,让她无法与外界联系,这是司法机关关心的问题,也是“违背妇女意愿”的一个标志。席阳确实也这样做了——朱斐报警后陈述,事发后,她想回家,席阳拿着手机不给她,后来他们出了门、上了车,手机依然在席阳那里,直到朱斐母亲打来电话。但席阳解释说,当时朱斐的情绪变得很不稳定,“我怕她乱来,就没给她手机”。
晚上7点多,席阳开着车,送朱斐回家。朱斐母亲没有让他们进家门,而是让席阳把车开到了僻静处——她说,那天,朱斐的三个哥哥都在家,她怕他们打席阳。她想和席阳谈谈,但当时她知道的信息很少,只是电话里朱斐的一句话,她被强暴了。
谈话时,席阳开了行车记录仪,朱斐和她母亲不知道。5月2日晚7点27分,录音开始。
这段谈话大概有半小时,一直是朱斐母亲在说话。她大概是这样讲的:
“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慢慢地交往,给对方安全感、信任感,(你这样)只能带来反感。”“你不该得到的,你提前得到了……你要把我闺女一生毁了,说明你原来都不打算娶,你不敢担这个责任。你要是现在做了(发生性关系),房本不敢那啥(加名),那你就是玩。你说玩,咱们就玩?
“明天民政局不上班,后天上班。后天我们去把结婚证领了,再写个约,把房本(加上朱斐的名字)……等(你家)下一批猪卖了,把钱(剩下的8.8万彩礼)给我拿过来。明年你们举行婚礼(2023年是朱斐的本命年,当地风俗认为,本命年不宜结婚),就行了。”
她说话的间隙,席阳一直在附和,表示同意。朱斐没怎么说话,一直在哭。半个小时录音里,就听见她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她跟母亲说,“妈,他不让我回家”。母亲希望把事了了,俩人尽快结婚,但朱斐说,“我不同意,我要是有啥变动呢?”她母亲问她,“能有啥变动?”
这场谈话结束9个月后,我和朱斐母亲谈起当时的情况,她解释自己的用意——发生这种事,女儿已经“平凡”了,不再纯洁了。她想缓和关系,毕竟双方订婚了,得“带着包容心”,但是该做的,男方也得做。“你已经把她女儿身给占了,你给她个名分,这是公道的呀。”她说自己不是为了钱,彩礼她一分不要,都让女儿带回去,“我走个过场,那也是咱的习俗”。谈话时,席阳态度挺好,她就觉得,行,知错改错,不是毛病。
转折发生在事发当晚。从这一晚开始,变成了两位母亲、两个家庭的战争。
晚上8点多,席阳到家,进门就找房本。母亲甄丽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了,他说,要给朱斐在房本上加名,他们发生了性关系。席阳把甄丽拉到车上,让她听行车记录仪的录音。听完,甄丽很生气,“把孩子吓成什么样了”,她觉得既然订了婚,(性关系)是可以发生的,但对方把它作为讨价还价的工具。
县城另一头的朱家,朱斐一直在哭,朱斐母亲心疼,也着急。她一直在等,等他们的电话,打来道歉,说他们会妥善解决、弥补,但她没等到——她说自己要的是一个态度,是尊重,是女儿婚姻的保障。
夜里10点多,她不想等了,主动打给甄丽,但甄丽说,他们成年了,订婚了,“发生这点事也正常吧”,她说自己女儿(席阳的姐姐)就在订婚后和未婚夫住在一起。这话让朱斐母亲很生气,“你们闺女这样正常,我家闺女这样就不正常”,这事不解决,她就报警。“你想咋弄就咋弄吧”,甄丽回复她。
晚上10点52分,朱斐母亲真的报了警。10点55分,警察打给席阳,是他姐姐接的电话,否认了强奸——为了保护儿子,甄丽把席阳的电话卡卸了,换到了自己手机上。无论谁想联系席阳,都由母亲代为回应。
事发第二天,5月3日,朱斐的大哥找到朱家,再次提议,给朱斐房本加名、付彩礼,两人结婚。但席家不同意,甄丽觉得被要挟了,“他们咄咄逼人,我接受不了”。朱斐的大哥愤怒地离开了,走时他说,自己在北京有房,在当地也认识人,甄丽回击他,“你看你开那车,5000块都没人要”。席阳的姐姐还报了警,告朱家诈骗,警方没有立案。
事发第三天,5月4日,情况有了变化——法律规定,刑事案件立案审查期不超过3天,如果3天内不撤案,就要进入司法程序。警方也不想把事情闹大,4号晚上,在阳高县一位民警的调解下,两个家庭达成了和解方案:第二天上午,双方在县城行政中心,签一份合同,男方承诺在房本上给朱斐加名,并注明共同所有,在公证部门公证,双方领结婚证,此事结束。
但很巧的是,房本不在当地,它被席阳姐姐带到了她的居住地北京。她要当天从北京赶回,送还房本。席家称,这是她拿其他文件时不小心带走的,但朱家认为,这就是故意的。
总之,5月5日上午,朱斐一家在民政局门口等到了快12点,席阳和他姐姐以及房本都没出现。朱家人生气地回了家。此后,该案进入司法程序。
在跟双方母亲的沟通中,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案发当晚,其实两位母亲都不太清楚事情的全貌。第二天早上,朱斐在家里穿着短袖,母亲看到她手臂上的淤青,才知道事发时,女儿遭受过暴力。而席阳的母亲甄丽,也不知道有强迫的情节,儿子只告诉她,他们“睡了”。两天后她到这间新房,才看到火烧过的窗帘、烧黑的柜子,这都是朱斐反抗的痕迹。但为时已晚。
这一对情侣,真正的当事人,事后也未进行深入的交流。所有的谈判和拉锯,都发生在长辈之间。
直到5月5号,席阳到了派出所,即将被拘留,警察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让他给朱斐打一个电话,两人的谈话是这样的——
席阳:我马上要被逮捕了,也不奢望你改变啥了。你记住,我出来还要娶你,还要追求你。
朱斐:你甭娶,我敢嫁吗?我不敢嫁了(哭),不用你娶。
席阳:你不要哭了,我出来之后还会找你的。
朱斐:你这是在威胁我吗……你别找我了,我想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你意思是让我搬家吗?
席阳:不是,真的不是,我也和你表态了,做了啥事,我也挺对不起你,你好好休息。
朱斐:我真不敢嫁了,你看看你做的啥?
席阳:我真的不做过。
朱斐:你的不作为,就是你做的。

污名
席阳被捕后,两个家庭的关系彻底撕裂,司法和舆论都成为了战场。
2024年1月,我们造访阳高时,看到两家人的院子外面都装上了摄像头。高高的院墙上,它们24小时工作,保卫家庭的安全。
为了营救儿子,甄丽后来还去过朱家,当时是检察院起诉阶段,如果朱家愿意出具和解书,检察院也还可以不起诉。但朱家母女没有让她进家门,也不同意和解。之后,甄丽又找了同村的106位村民,在联名信上签字,证明席阳性格脾气好,不是坏人,试图表达一些“民意”,但这没有影响一审判决。

2023年8月,有媒体发布了关于该案的第一篇报道,标题是《回门宴婚房发生关系后女方控告被强奸,男方已被羁押105天》。这篇报道主要引述了甄丽的讲述,而她提供的一些信息,让该案受到更广泛的关注——
比如18.8万的高额彩礼;两人曾在婚房同居、房中有女方的生活用品;两人事前在电梯亲密搂抱;席阳始终说女方是自愿的;事后女方借机施压等等……女方家属在这篇报道中只出现了一句,朱斐的母亲说,“他强奸了我女儿”。
此后的几个月里,围绕这个案件,更多的谣言出现了。
阳高县法院在《答记者问》里也专门澄清过:比如“骗婚”“以告强奸进行敲诈”“订婚发生关系后第4天,女孩控告强奸”“双方当事人为同居关系”“被害人有过婚姻史”“被害人给婚介所3万元介绍费”,这些传言均为不实信息。
很多讨论都围绕这18.8万的彩礼展开。网友会想象,为什么女方要这么高的彩礼?是因为她有三个哥哥,彩礼要拿来给他们娶妻,但其实,她的三个哥哥都已结婚;还有人会说,这案子之所以发生,归根结底就是高彩礼,男方举全家之力娶到的妻子,会默认有对她的处置权,这会让女性在婚内的尊严和权利受损。
在这个县城里,相隔几公里,两个家庭在这种对立中,想象出彼此更多的不堪。
朱家始终沉默,从未主动对外发声。就像2025年4月16日大同中院的审判长《答记者问》里说的,“被害人选择相信法律,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谢绝所有上门媒体的采访,拒绝舆论炒作”。但所有的网络讨论,他们都看到了。朱斐的母亲告诉我,她看到那些谣言很伤心,“多损啊”,她女儿没谈过恋爱,成了她人口中二婚、三婚的“坏女人”。
她觉得真正骗婚的是席阳一家。最初相亲时,席阳资料填的是大专,后来她才知道,席阳是中专毕业。她说,如果知道他是中专学历,他根本连女儿的面都见不到。
或许是因为长久的防御状态,这位母亲对陌生人很警惕。此前有记者去找她,她会说,自己得了传染病,不能开门见人。在我拜访时,她开了门,但也会问,我们是不是对方派来的探子?
对席阳的母亲甄丽而言,煎熬同样强烈。她的儿子正在看守所。她经常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为他家辩护的自媒体文章。为了给儿子翻案,她也选择了拥抱舆论——这起案件涉及隐私,核心案情不宜对外公开,但她还是一直在网络发布消息。大同中院的《答记者问》里提到,她多次发布涉及被害人隐私的信息,因此,二审期间,法院对她进行了训诫。
我在阳高时,也曾听到法官打电话给她,让她必须删帖,否则她会受到处罚。她立马答应对方,但是转头就说,没事,传播效果已经达到了。
一个爱儿子的母亲眼里,看到的或许是她愿意看到的、不完整的真相。
甄丽会告诉我,她听说女方家里有很多丑闻。那是民间社会常见的污名,对女性私生活的攻击,指向朱斐母亲,也指向朱斐,她说,朱斐可能生过病、结过婚,也会说,怀疑她家后台硬、有关系。
至于核心案情——席阳是否真的强奸,她反复说,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告诉她,自己看了案情,这个案子里没有暴力。
她也会在漫长的时间里,不断想象这个她还并不熟悉的女孩。她告诉我,他们虽然只认识三个月,但“几乎天天在一起”,朱斐还会在房子里洗澡,“那么年轻的、热恋中的两人,女方在里面洗澡,他们能干啥 ?”但无论是席阳、朱斐的陈述,还是朱斐的身体检查都证明,他们此前未发生性关系。且从聊天记录来看,他们也经常几天不见面。
甄丽(包括很多网友)也会质疑,既然朱斐不愿意,那为什么只有手臂有淤青?如果她强烈反抗,她应该会阴道撕裂,她完全可以打席阳,攻击他,让他停手。
但一位来自某中部城市公安局的刑警告诉我,女方阴道是否撕裂,是否强烈抵抗、攻击男方,男方身上有否有伤,并非强奸罪的构成要件——尤其,这起案件不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而是发生在亲密关系里。

看不见的女儿
最后该谈谈朱斐了。这场悲剧里,她始终是一个模糊的人。作为受害者,过去这两年,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她有一个抖音账号,是个小号,只和几个相熟的朋友互动。2024年初,她还比较活跃,有时会发自己简单的跳舞视频,她眼睛很大,头发长,嘴巴弯弯的,笑起来很好看。
但检视案发后的所有记录,朱斐相当沉默,出现时常常在哭。案发当晚,母亲和席阳在车里讨论怎么善后时,她哭,说自己“不愿意”;她后来告诉母亲,发生了这种事,就算最后真的领证了,她也不想和席阳同居;案发四天后,席阳在公安局,最后一次打电话给她,她也一直在哭,说不敢嫁了。
对家庭,她有一种顺从和依赖。母亲37岁生下她,独自抚养她,是某种权威般的存在。让她离开太原回老家,她照做了;让她23岁就相亲,她也同意了;叮嘱她不能有婚前性行为,下午6点前回家,她也认同;最后被顺势推着订婚,至少在订婚宴上,她是笑着的,没表现出犹疑或沮丧。
但在某些时刻,她有她的刚烈。与席阳相处时她很讲原则,说好的事情,如果对方食言,她会很生气。5月2日,强奸案发生后,她反锁了卧室门,打算跳楼,结果窗户装了铁丝网,席阳把门踹开,把她拉下来。她后来告诉母亲,为什么她又点燃了窗帘——席阳不让她走,她觉得如果着火了,邻居看到了,会报警,这样她就会得救。

2024年1月,在她家院门口,她母亲说,没办法邀请我们进门,而且我们得小声说话,因为朱斐在家,她精神状态不好,不愿和外面的人接触,怕刺激到她。
案发后,朱斐的精神一直不太稳定。在公安局做笔录时,她母亲也告诉过警察,朱斐晚上睡觉时会惊厥,“一会儿瞎叫,一会儿哭,要么就是很冷漠,不说话”。吃饭比以前少,睡觉也睡不好,要靠吃药入眠。家里想带她去医院看看,她反应很激烈,“一到医院,弄也弄不住她”。
她这样的状态,也无法工作,据她母亲说,她要么待在家里,要么就出去散心,去亲戚家或同学家,有段时间她离开阳高,去了太原。
这起案件的一审和二审,朱斐都没有出庭,朱家表示,她的精神状态不稳定,无法出庭。另一边,席家不断释放信息、把案件一次次推上热搜。律师的朋友圈里,常常分享这起案件冲上热榜的截图。
2024年1月,席家启动了对朱家的民事诉讼,想要拿回最初付的10万元彩礼,以及戒指等一万多元的花费。在上诉状里,他们写到,“原告席阳仍幻想与被告朱斐喜结连理、永结同心、白头到老、共度余生,由于无法与其取得联系,现通过诉讼的方式,向被告提出结婚请求”。这样写的原因,是2024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份关于彩礼纠纷案件的规定,按规定,如果朱斐不愿与席阳结婚,且她没有和席阳长期共同生活过,那么她应该退还这笔彩礼。
我和朱斐的母亲见面时,不可避免地谈到了这笔彩礼。她语气里有压抑许久的愤怒:退钱可以,但女儿所承受的谣言和污名,她要一个公开的道歉。“物资、戒指、钱,都可以退。你给我一个公道的道歉,我会一分不差还给你。”很快,她把收到的10万元彩礼和7.2克金戒指,送回了婚介所,让对方转交给席家,但甄丽没有取回,执意上诉。
在这个案件里,朱斐和她的家庭表现出了克制和刚强。她的反抗足够强烈,退回了彩礼,坚决推进司法程序。那句“不”,说得很清楚,也付出了代价——困在审判里的两年时间,和难以计量的精神创伤。
我们最后一次得到她的消息,是2024年春天,她改掉了社交平台的名字,删掉了过往所有动态,关闭了与外界的小小的窗口,划定了边界。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朱斐、甄丽、席阳均为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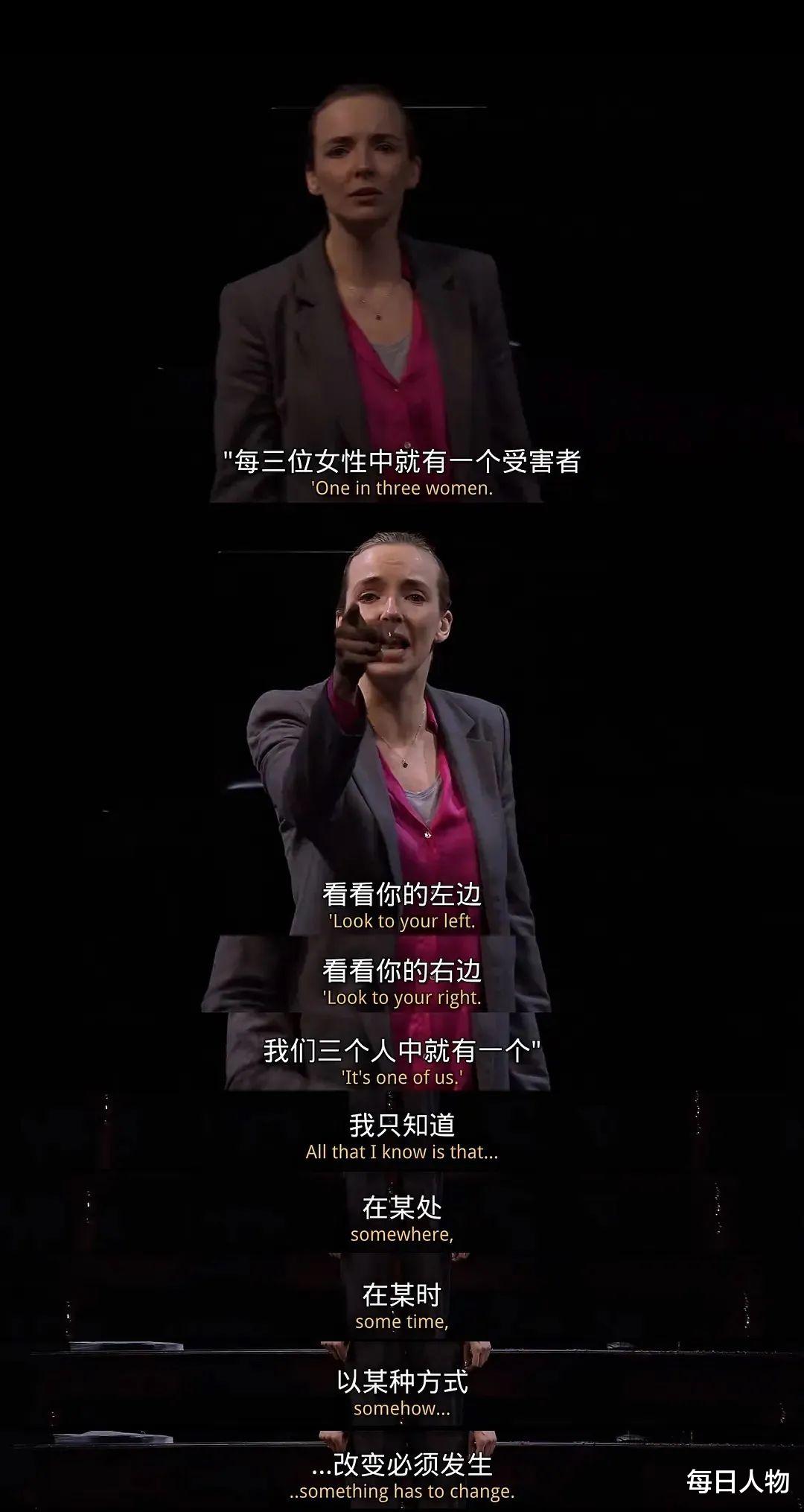
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侵权必究
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请发送邮件至 203304862@qq.com
本文链接:https://jinnalai.com/jingyan/743861.html

